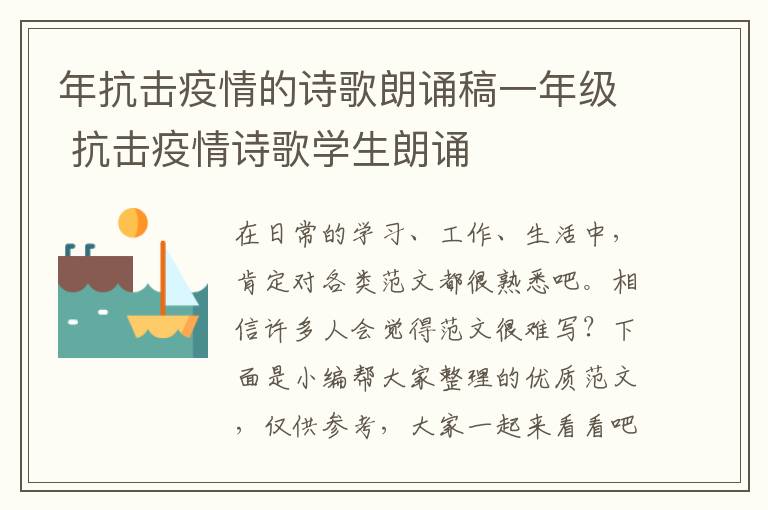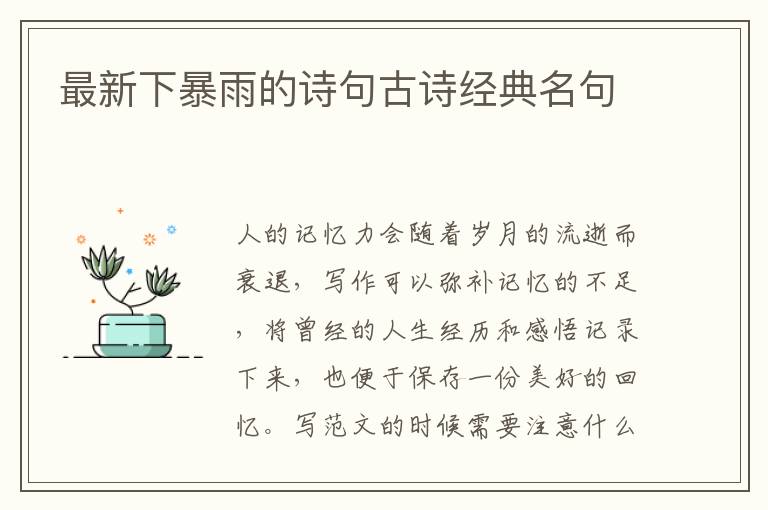鐘叔河《悼亡妻》隨筆

悼亡妻
妻亡于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當(dāng)天發(fā)出的哀啟,是匆匆寫成,由周實(shí)和王平兩位朋友幫忙快印發(fā)出的,全文如下:
我妻朱純已于本日凌晨二時(shí)去世,終年七十九歲。
零四年十月朱純查出癌癥,當(dāng)時(shí)即已擴(kuò)散,預(yù)告兇險(xiǎn)。她卻從容面對(duì),說“五七年沒打垮我,七零年沒打垮我,這次病來得兇,人又老了,可能被打垮,但垮我也不會(huì)垮得太難看,哭哭啼啼”。零五年九月她預(yù)立遺囑,說她只要能動(dòng),就會(huì)活得快樂。兩年多來的情形,確實(shí)如此。
朱純一九二八年生于長(zhǎng)沙河西,四九年八月進(jìn)報(bào)社當(dāng)記者,五三年和我結(jié)婚。五七年后夫妻協(xié)力勞動(dòng)維生,她成了五級(jí)木模工。“文革”中我坐牢九年,她獨(dú)力養(yǎng)大了幾個(gè)孩子,送了我母親的終。五十四年來,她照顧我和孩子遠(yuǎn)比照顧自己為多,最后對(duì)我說的一句話還是:“你不要睡得太晚。”
朱純一生樸實(shí)謙和,宅心仁厚。我的朋友都是她的朋友,對(duì)我有意見的人對(duì)她也沒意見。連家中的保姆,無論去留,從沒有說她不好的。
朱純能文,但無意為文,離休后才偶然寫寫,有《悲欣小集》,亦不愿公諸于眾,只印示生平友好。病后這兩年多,她卻發(fā)表了不少文章,最后一篇《老頭挪書房》刊載于本月十一日《三湘都市報(bào)》,文中仍充滿對(duì)生活和親人的熱愛,她自己卻在文章見報(bào)十天后便永別親人和生活了。
此時(shí)此刻,我和女兒們自然是極為悲痛的,但仍謹(jǐn)遵遺囑,只將哀啟發(fā)送給至親好友和關(guān)心過她的人,不舉行任何儀式,家中也不設(shè)靈堂,請(qǐng)大家不必來函來電更不必親臨。只請(qǐng)知道這回事:朱純已走。如果覺得她還好,是個(gè)好人,在心里記得她一下,就存歿均感了。
也是因?yàn)橛信笥褞兔Γ俜莅ⅲ簧衔绫慵陌l(fā)完了。
朱純從來是一個(gè)快樂的人,雖罹惡疾,仍能不失常態(tài),最后一次進(jìn)醫(yī)院之前,也不怎么顯露病容。入院前半月還曾下鄉(xiāng)游玩,和我商量想在鄉(xiāng)下找一間小屋住住,說“這不花多少錢,但得裝上寬帶網(wǎng),好在電腦上和女兒、外孫女兒見面交談,再寫寫文章”。
生病的這兩年,的確是她寫作最多的兩年,一直寫到去年年底的《老頭挪書房》。
我于妻去世后出版的《青燈集》,一百二十三篇文章中的一百一十篇,都是妻在病中幫我打印,有的還幫我潤(rùn)色過的。她走了以后,過了八十天,我才勉強(qiáng)重拿筆桿,不到兩千字的《談毛筆》,前后竟寫了四天……
朱純病中還催著我“挪書房”,即是將客廳改為一間大書房,把擠在內(nèi)室里的書大部分搬出來,騰出兩間“工作室”。她原有一臺(tái)電腦,又叫女兒買來一臺(tái),督促我“總要學(xué)會(huì)用才好”。可是如今,兩臺(tái)電腦擱置在兩間空蕩蕩的“工作室”里,我則只能像楊絳先生來信勸勉的那樣,“且在老頭的書房里與書為伴”了。
妻走了,五十多年來我和她同甘共苦的情事,點(diǎn)點(diǎn)滴滴全在心頭,每一念及,如觸新創(chuàng),總痛。
《青燈集》印成后,南方冰凍,運(yùn)輸不通,幸得有關(guān)同志特別關(guān)照,以航空快遞寄來,才使我能以新書一冊(cè),送到她托體的山樹下,以此作為她的周年祭。當(dāng)時(shí)我在心中反復(fù)默禱著道:
“朱純啊,我不久就會(huì)來陪伴你的,你就先在這兒看看書,好好地休息吧。”
(二零零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