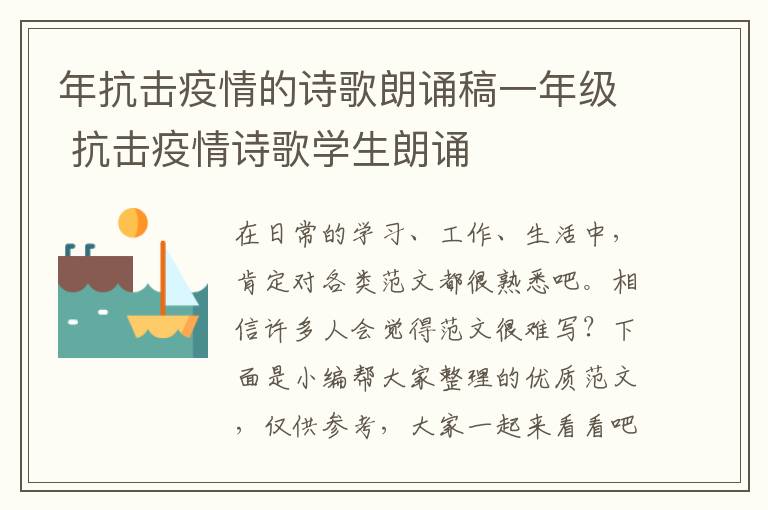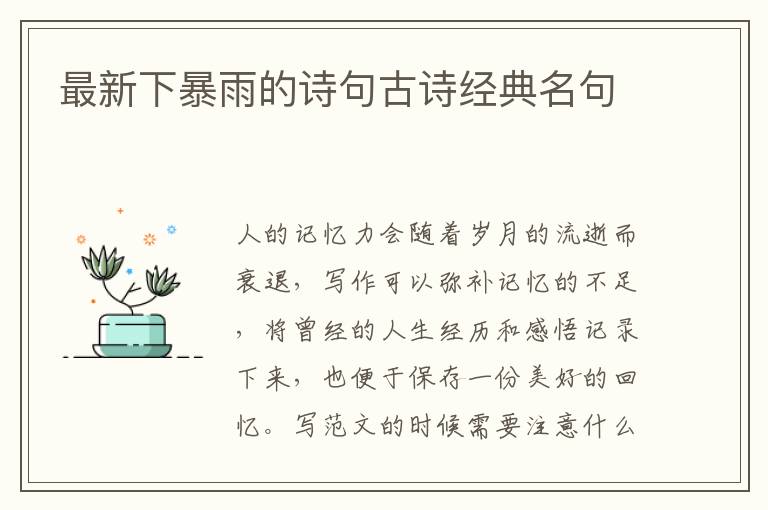鐘叔河《盛世修史》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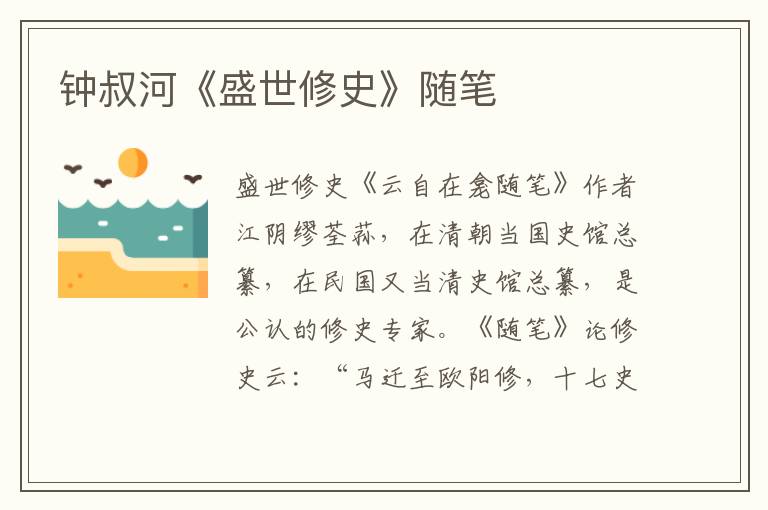
盛世修史
《云自在龕隨筆》作者江陰繆荃蓀,在清朝當國史館總纂,在民國又當清史館總纂,是公認的修史專家。《隨筆》論修史云:“馬遷至歐陽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筆,雖美惡不等,仍各有體裁”;后來《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體例參差,掛漏甚多,“此人多手雜之故也”。可見繆氏并不認同“人多好辦事”,并不主張靠“眾人拾柴火焰高”的辦法來修史。
時行說“盛世修史,明時修志”。在說修史之前,先說說修志吧。日前購得一部大書《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冊,一九九八年北京出版,卻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間修成的。據介紹:北京市政當局一九三八年秋設立修志處,撥款一萬馀元,處長由市政府秘書長兼任,派秘書一人總管處內一應事宜,聘任總纂、分纂和特約編纂夏仁虎等十馀人分撰十四門三表,一人擔任一門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馀萬字,至一九三九年秋(僅僅一年時間),除《故宮志》一門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這是不是粗制濫造的偽劣產品呢?卻并不是。新寫的出版說明云:“此書不僅廣泛蒐集了前代的文獻,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國時期的史料,有著無法比擬和不可取代的價值。”我瀏覽了一下《藝文志》和《藝文志補》,所收約兩千種關于北京“地與人”著述的目錄和提要,比到國內任何圖書館去檢索能得的多得多。《禮俗志》中記北京本地小吃,“驢打滾乃用黃米面蒸熟,紅糖為餡,滾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廟會集市時,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賣,近年則少見矣”,也寫得津津有味。持與近年所出志書相比,說它“有著無法比擬和不可取代的價值”,似乎并非過譽。
現今修史的詳情無從知悉,修志的情況則多少曉得一些,即拿湖南省的“新聞”“出版”二志而言,這兩冊最多頂得《北京市志稿》中的兩冊吧,而所花的人力、財力、時間,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北京斷非盛世明時,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聽說蘇聯研制秘密武器,設計者多為本國的犯人和敵國的俘虜,嚴密監管下不僅工效特高,保密也放得心,難道夏仁虎他們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下創造高效率高質量的么?
當事人的說法又否定了這種臆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蘇晉仁先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參加過《北京市志稿》的編纂,一九八八年又為《志稿》出版寫了總序。他說,當時的總纂、分纂諸人“大都為學術界名流學者,各有專長,因而待遇優厚,禮敬有加”。“這些老輩不但對史例的制訂,條目的安排,史料的選擇,人物或事件的評騭各抒己見,互相切磋,且從善如流,吸收年輕人來從事工作”(蘇先生當時便只二十幾歲),“所以如此龐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內竣工”。既然“禮敬有加”,當然不會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優厚”,則肯定要在一萬元之外加辦“特供”。
現在該“點題”來說說“盛世修史”了。近見報紙刊載:“十年中將有幾千名清史研究學者參與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標的模式由各界承包,總經費至少在六億元以上。”幾千人和繆荃蓀認為“人多手雜”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億元則是一萬元的六萬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況。只不知盛世的司馬遷、歐陽修是誰?如今的繆荃蓀又在哪里?他們會不會來投標承包呢?
(二零零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