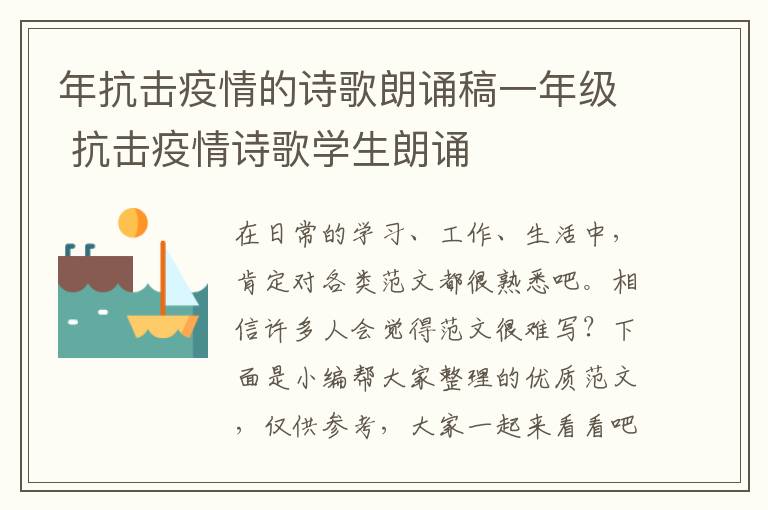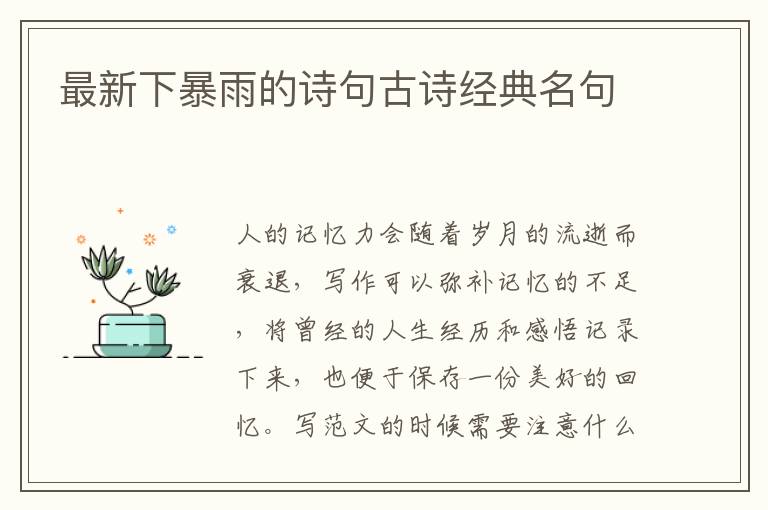潘圖體詩(shī)歌

潘圖體詩(shī)歌
這種體裁的詩(shī)歌長(zhǎng)短不定,每一詩(shī)節(jié)由四個(gè)詩(shī)行組成,其第二行及第四行作下一詩(shī)節(jié)的第一行與第三行,以此類推,直到最后一節(jié)為止。在最后一節(jié)詩(shī)中,全詩(shī)的第一行又用作為它的結(jié)尾一行。在有些英國(guó)潘圖體詩(shī)歌中,全詩(shī)的第三行用作最后一節(jié)的第二行。因此,這種詩(shī)歌的開始與結(jié)尾都是同一個(gè)詩(shī)行。該詩(shī)體的另一個(gè)顯著的特點(diǎn)是,不同的主題必須同時(shí)在全詩(shī)各部分同時(shí)展開;每節(jié)的前兩行是一個(gè)主題,后兩行是另一個(gè)主題,兩對(duì)詩(shī)行只是在音韻上互相聯(lián)結(jié)。
潘圖詩(shī)體原是馬來亞的一種詩(shī)歌形式,最早由法國(guó)的東方學(xué)者厄內(nèi)斯特·福伊內(nèi)引入西方詩(shī)歌,后由維克多·雨果在其詩(shī)集《東方吟》的注釋中將這一詩(shī)體形式確定下來。法國(guó)文壇中擅長(zhǎng)此體的詩(shī)人有邦維爾、西埃費(fèi)爾、李斯勒以及波德萊爾等。雖然這一詩(shī)體源于東方,而且西方接受較遲,但它經(jīng)常被人們與法國(guó)較古老的一些詩(shī)體,如回旋體、八行體、三節(jié)聯(lián)韻體、田園歌體等相提并論。批評(píng)(Criticism)
一、批評(píng)的功能
和本文第二部分(即“批評(píng)的種類”)相比,這一部分篇幅較短,內(nèi)容少,理論性強(qiáng)。本文對(duì)批評(píng)的分類是以其可能具有的目的為根據(jù)的,這種區(qū)分方式打破了各個(gè)流派的界限。批評(píng)的功能可分為四種(也有人認(rèn)為是五種),即:技巧的,社會(huì)的,實(shí)用的和理論的。還有一些與此有關(guān)的目的,但嚴(yán)格地講,它們不屬于批評(píng)的范疇。
1.技巧批評(píng)
技巧批評(píng)是指對(duì)具體寫作實(shí)踐的指導(dǎo)。這種批評(píng)尚無公認(rèn)的術(shù)語(yǔ),我們還可把它稱為“寫作課式”批評(píng),“說教式”批評(píng),“實(shí)用式”批評(píng),甚至“創(chuàng)作式”批評(píng)。后者容易和卡萊爾及蘭姆采用的批評(píng)方式相混淆,他們往往由于有創(chuàng)作的沖動(dòng)卻苦于無法表達(dá)而使用批評(píng)性論文作為表達(dá)這種沖動(dòng)的一種形式。技巧批評(píng)在伊麗莎白女王時(shí)代十分流行。喬治·加斯科因的《英語(yǔ)韻文寫作指導(dǎo)》的標(biāo)題就揭示了他撰寫該文的目的。帕特納姆的《英國(guó)詩(shī)歌的藝術(shù)》告訴我們,其目的是“指導(dǎo)淑女……和悠閑的朝臣偶然寫點(diǎn)快活小調(diào)”。今天嚴(yán)肅的批評(píng)家對(duì)他們的做法不屑一顧。我們由于對(duì)藝術(shù)的獨(dú)創(chuàng)性無比尊重,而不再相信幾句空泛的說教能為學(xué)習(xí)寫詩(shī)的人提供真正的有益的幫助。做詩(shī)的規(guī)則也許有點(diǎn)意義,但就一首詩(shī)的目的而言,這些規(guī)則是批評(píng)家最少考慮的。
間接的技巧批評(píng)更重要。大部分批評(píng)者對(duì)現(xiàn)有作品進(jìn)行批評(píng)的目的之一是對(duì)尚未寫成的作品提出間接指導(dǎo)。唐納德·戴維宣稱他的《純潔的英國(guó)詩(shī)歌用語(yǔ)》是專門寫給“未來”的詩(shī)人的。龐德和艾略特是這類批評(píng)的代表。艾略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龐德早期的批評(píng)文章主要是寫給“風(fēng)格尚未形成的年輕詩(shī)人”的。其實(shí),不僅在龐德的批評(píng)中,而且在艾略特的大部分詩(shī)歌中都流露出對(duì)詩(shī)的未來發(fā)展的巨大關(guān)注。他的詩(shī)作《休·賽爾溫·毛伯利》和譯作《水手》的可鑒之處僅僅是其風(fēng)格對(duì)年輕詩(shī)人有所啟迪。艾略特在這篇文章中說:“我最好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是我個(gè)人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副產(chǎn)品。”這不一定能說明他應(yīng)用的是技巧批評(píng),因?yàn)槲覀冴P(guān)心的是批評(píng)的功能,而不是其來源。但是艾略特在提醒人們注意法國(guó)象征主義詩(shī)人和18世紀(jì)的玄學(xué)派詩(shī)人有著共同之處時(shí),他的目的不僅是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這些詩(shī),而且為現(xiàn)代英語(yǔ)詩(shī)歌的發(fā)展揭開了新的一頁(yè)。因此盡管艾略特對(duì)玄學(xué)派詩(shī)歌的理解并非無懈可擊,然而他或其他人應(yīng)用這種理解(或者誤解)進(jìn)行批評(píng)的方式,卻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
2.社會(huì)批評(píng)
重要的是詩(shī)歌應(yīng)該有意義,而且應(yīng)該對(duì)社會(huì)有意義,因此文學(xué)批評(píng)應(yīng)該重視作品的社會(huì)作用,幫助文學(xué)建立受人尊敬的地位。這個(gè)任務(wù)可以在不同水平上完成。從最低層次上講,書籍只要有人評(píng)論,不論說些什么,都是有益的。日?qǐng)?bào)、周刊的書評(píng)欄的作用不僅僅是對(duì)一些書籍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而是吸引人們對(duì)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不間斷的討論。從高一點(diǎn)的層次上講,這種社會(huì)功能在于喚起人們對(duì)文學(xué)的熱情。羅伯特·林德、德斯蒙德·麥卡錫、菲利浦·湯因比等作家和知名學(xué)者亞瑟·奎勒一庫(kù)奇爵士等人的文章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閱讀他們的文章使人了解他們的人格,傾聽他們真誠(chéng)地?cái)⒄f自己對(duì)文學(xué)的厚愛。當(dāng)然,這種文章的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過分袒露自己對(duì)文學(xué)的熱情容易導(dǎo)致虛張聲勢(shì);大談特談對(duì)文學(xué)的熱愛無異于嘩眾取寵;一味取悅讀者難免流于庸俗無聊。盡管如此,只要這類文章能夠促使讀者閱讀并討論所讀的書籍,其作用就是令人贊賞的。這類批評(píng)若是對(duì)一部書做出有分量的評(píng)論,就變成了實(shí)用批評(píng),若是系統(tǒng)地評(píng)論文學(xué)的重要性和價(jià)值,就成為了理論批評(píng)。
3.實(shí)用批評(píng)
實(shí)用批評(píng)是指對(duì)具體作品的認(rèn)識(shí)研究。實(shí)用批評(píng)并不古老。18世紀(jì)以前針對(duì)某一具體的文學(xué)作品的評(píng)論還是鳳毛麟角,即使有也不詳盡,而且缺少真知灼見。艾迪生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旁觀者》雜志上率先撰文評(píng)論彌爾頓的《失樂園》。與此同時(shí),威廉·理查遜和莫里斯·摩根也開始評(píng)論莎士比亞的作品,但是,實(shí)用批評(píng)的真正的創(chuàng)始人卻是柯爾律治。從他的身上,我們首次發(fā)現(xiàn)了“新批評(píng)”派的典型特征:仔細(xì)研讀作品以掌握要旨,并且引述細(xì)節(jié),周密論證。
柯爾律治在《文學(xué)傳記》中評(píng)論了華茲華斯的詩(shī)作和莎士比亞的《維納斯和阿多尼斯》,如果他把這些評(píng)論以及他的一些關(guān)于莎士比亞的講演,寄給《細(xì)繹》和《肯尼恩評(píng)論》的編輯們,他們肯定會(huì)如獲至寶。而人們可以想象他們?cè)诮拥桨仙u(píng)論彌爾頓的文章時(shí)則會(huì)猶豫不決。然而即使是柯爾律治的評(píng)論也夠不上現(xiàn)代實(shí)用批評(píng)的典范;而19世紀(jì)的著名批評(píng)家如巴杰霍特、佩特、阿諾德等人的評(píng)論也使我們感到是差強(qiáng)人意的,或者認(rèn)為這是由于他們的批評(píng)目的和我們的不盡一致。例如,阿諾德檢驗(yàn)文學(xué)作品的“標(biāo)準(zhǔn)”初看起來和現(xiàn)在流行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方法很相似,然而,他的比較僅僅是啟蒙性的,并不像現(xiàn)代著名的批評(píng)家那樣,仔細(xì)挑選作品,精心比較其相似之處。
嚴(yán)格意義上的實(shí)用批評(píng)形成于20世紀(jì)。1920年的一天,I·A·理查茲在劍橋大學(xué)向?qū)W生分發(fā)了未署名的詩(shī)作,讓他們議論和評(píng)價(jià)。學(xué)生們的評(píng)論讓人震驚:在雜志上發(fā)表作品的末流詩(shī)人被吹得天花亂墜,而多恩·霍普金斯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等著名詩(shī)人卻遭到無情的謾罵和詆毀。學(xué)生們對(duì)妙語(yǔ)佳句無情嘲弄,而對(duì)荒唐蹩腳的詩(shī)行推崇備至。理查茲在《實(shí)用批評(píng)》一書中描述了上述實(shí)驗(yàn),并且討論了困擾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主要問題。這本書和它的續(xù)篇《教學(xué)中的解釋》已經(jīng)成為英美各大學(xué)從事批評(píng)實(shí)踐的標(biāo)準(zhǔn)資料中的一部分,其方法是:仔細(xì)閱讀原作。學(xué)院以外的一批詩(shī)人如格雷夫斯、T·S·艾略特、燕卜蓀等也加入了這一潮流,爭(zhēng)相撰文。艾略特的《圣林》(1920)成為本世紀(jì)影響最大的批評(píng)論文集。格雷夫斯和萊丁合寫的《現(xiàn)代派詩(shī)歌概述》不僅評(píng)論了莎士比亞,而且也評(píng)論了霍普金斯和E·E·肯明斯。他們的文章對(duì)燕卜蓀影響頗大。燕卜蓀后來寫了多篇精細(xì)入微而又富有挑戰(zhàn)性的文章。他致力于挖掘詩(shī)的隱秘含義,研究雙關(guān)語(yǔ)、諷刺和語(yǔ)義含混的詞句。《晦澀的七種類型》(1930)就是他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燕卜蓀的基本信念是,卓越的詩(shī)歌都是復(fù)雜深?yuàn)W的。“任何時(shí)候,讀者若被簡(jiǎn)單明白的詩(shī)行深深打動(dòng),真正打動(dòng)他的是詩(shī)行部分地再現(xiàn)了他往日的經(jīng)歷和往日的判斷的結(jié)構(gòu)”。果真是這樣,實(shí)用批評(píng)家便有了大加發(fā)揮的余地。加入實(shí)用批評(píng)潮流的還有F·T·利維斯、克利恩斯·布魯克斯、R·P·布萊克默、蘭塞姆和奈茨。利維斯堅(jiān)持認(rèn)為,批評(píng)家應(yīng)禁止使用與具體作品毫不相干的空話。他的批評(píng)出色地貫徹了這一主張。他主辦了21年的刊物《細(xì)繹》,不僅在名稱上而且在內(nèi)容上體現(xiàn)了他的一貫主張。布魯克斯的批評(píng)文章,他與羅伯特·潘·華倫合寫的大學(xué)教材《理解詩(shī)歌》一書奠定了他的地位,也使他成為這一批評(píng)派中的佼佼者。
實(shí)用批評(píng)既是一種目的又是一種方法。作為方法,它要求人們批評(píng)時(shí)必須緊扣原文;作為目的,它與教學(xué)法相似,是為了幫助讀者欣賞詩(shī)作。讀者一旦能夠欣賞一首詩(shī),評(píng)論就無關(guān)緊要了,就像詩(shī)人一旦把要寫的內(nèi)容寫成詩(shī)后,技巧批評(píng)就失去了意義一樣。當(dāng)然,這種目的是建立在一種假設(shè)之上,即對(duì)一首詩(shī)有一種所謂的“正確”理解之上的,批評(píng)的目的就是將讀者逐步引向這個(gè)正確的理解。實(shí)用批評(píng)的反對(duì)者駁斥的也正是這一點(diǎn)。
激烈的反對(duì)者認(rèn)為,文學(xué)鑒賞既然是主觀的,那么每個(gè)人的理解只是對(duì)他自己而言是正確的。如果兩個(gè)人對(duì)一首詩(shī)的意義或價(jià)值產(chǎn)生了分歧,就每一位而言,都是正確的。F·L·盧卡斯是這種論點(diǎn)的激烈倡導(dǎo)者。這種觀點(diǎn)就字面理解,會(huì)使文學(xué)討論變得無益。既然沒有外在的標(biāo)準(zhǔn),重新仔細(xì)閱讀原著便沒有意義,因?yàn)槿藗儾槐匦拚吞岣咦约旱恼J(rèn)識(shí)。查爾斯·莫里斯在理論上反駁了上述觀點(diǎn),他提出了“主觀意識(shí)相互聯(lián)系”的論點(diǎn),認(rèn)為在實(shí)踐中,即使是最激烈的相對(duì)論者也會(huì)偏重某些讀者對(duì)一首詩(shī)的理解,而不會(huì)把所有的理解都看成是同等重要的。
一種較為溫和的然而卻更嚴(yán)肅的反對(duì)觀點(diǎn)認(rèn)為,文藝作品的價(jià)值是隨著每一代讀者的變化而變化的。T·S·艾略特說,當(dāng)一件新的藝術(shù)品被創(chuàng)作出來之時(shí),“這件藝術(shù)品之前的所有藝術(shù)品也隨之發(fā)生了某種變化”。韋勒克和華倫在討論文學(xué)作品的存在方式時(shí)(見《文藝?yán)碚摗?從理論上對(duì)艾略特這一觀點(diǎn)做了最好的闡述;艾略特也用自己的詩(shī)歌的影響為此做了完美的例證。這種觀點(diǎn)會(huì)很自然地導(dǎo)致歷史相對(duì)論,會(huì)使人相信“凡是值得翻譯的古典詩(shī)歌每過50年都應(yīng)重譯”,也會(huì)使人們認(rèn)為,每一代讀者都是用自己的方式閱讀古典名著。
如果說某一個(gè)時(shí)代本身只有一種正確的理解,這種回答是不夠的。時(shí)代相互重疊,而初看是荒誕不經(jīng)的理解也許標(biāo)志著一種新思潮的興起,或者預(yù)示著舊思潮的衰亡。用年代劃分一代一代的讀者必然要包括不同社會(huì)、不同觀點(diǎn)的讀者,例如天主教徒、自由派的人道主義者以及當(dāng)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甚至還應(yīng)包括不同性格的讀者。我們除了要求有某種正確的理解外,還必須假定有一個(gè)理解的范疇:它應(yīng)該容忍那些令人懷疑的、怪異的,甚至荒唐的理解,容忍那些帶有傾向性的,和我們的觀點(diǎn)相左的,甚至守舊的、過時(shí)的理解。在“合法”的理解之中到底允許多大程度的“背離”,這有賴于作品本身。坎皮恩、蘭德爾或者豪斯曼的抒情詩(shī)很可能只有一種正確的理解,甚至不會(huì)因?yàn)闀r(shí)代的變化而有多大變化。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李爾王》等則迥然不同,可以自圓其說的理解數(shù)不勝數(shù)。就《李爾王》而言,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是因?yàn)樗w現(xiàn)的經(jīng)驗(yàn)異常恢弘,內(nèi)容異常豐富,而《哈姆雷特》除了以上的特點(diǎn)外,它本身的模棱兩可也是導(dǎo)致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假設(shè)實(shí)用批評(píng)不僅影響我們對(duì)一首詩(shī)的理解,而且影響我們對(duì)它的判斷,這樣就駁斥了那種認(rèn)為理解和判斷是兩種互不相關(guān)的批評(píng)功能的觀點(diǎn)。我們至少可以認(rèn)為,對(duì)一首詩(shī)真正的全面的解釋一定是評(píng)價(jià)性的;在我們考慮一個(gè)語(yǔ)句的確切意義和聯(lián)想、它與整體的關(guān)系,或一首詩(shī)的節(jié)奏和形式特點(diǎn)的效果時(shí),我們要么認(rèn)為它取得了好的效果,要么指出它在藝術(shù)手法上有缺陷。一種純粹的判斷性批評(píng),如果對(duì)細(xì)節(jié)不加討論,它便失去了意義。判斷批評(píng)也許是實(shí)用批評(píng)的副產(chǎn)品和結(jié)論,離開實(shí)用批評(píng)它便無法存在。
實(shí)用批評(píng)到底前景如何?假若兩個(gè)讀者對(duì)一首詩(shī)的理解迥然不同,其中一個(gè)說服了另一個(gè),使后者承認(rèn)他誤解了原作,這樣一來,他們的觀點(diǎn)便協(xié)調(diào)了嗎?也許我們應(yīng)當(dāng)假設(shè),他們雖然讀的是同一首詩(shī),尋求的卻是不同的東西。C·S·劉易斯不同意利維斯關(guān)于《失樂園》的風(fēng)格的觀點(diǎn),他說,利維斯“見而憎恨之處正是我見而喜歡之處”。如果說這是在文學(xué)上持不同見解的一個(gè)典型例子,實(shí)用批評(píng)家便沒有多少作為了。但是,如果讀者的文學(xué)素養(yǎng)基本相同,只是在判斷一首詩(shī)的意義上有能力高下之分,那么,實(shí)用批評(píng)家便有了用武之地。對(duì)缺乏實(shí)用批評(píng)家那種敏銳的眼光、生活經(jīng)歷和專業(yè)知識(shí),或者沒有機(jī)會(huì)及大量的時(shí)間去研究一部作品的讀者,實(shí)用批評(píng)家便可以起到開導(dǎo)啟蒙的作用。
4.理論批評(píng)
這種批評(píng)所考慮的是文學(xué)是什么的問題。理論批評(píng)把“富于想象力的”或者“創(chuàng)造性”的文學(xué)作品與科學(xué)、宣傳、消遣讀物或者回憶錄等區(qū)別開,也把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xué)和低劣文學(xué)區(qū)別開。實(shí)用批評(píng)所關(guān)心的是:“這首詩(shī)有什么意義?”“這是一首好詩(shī)嗎?”而理論批評(píng)關(guān)心的卻是:“構(gòu)成詩(shī)歌價(jià)值的是什么?”第一部偉大的理論批評(píng)著作是亞里士多德的《詩(shī)學(xué)》。朗吉努斯的《論崇高》就意圖而言,也可以看做是理論批評(píng)著作。詩(shī)辯類的文章自古以來就十分流行,它們都傾向于系統(tǒng)地為詩(shī)歌辯解,因此都提出文學(xué)和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本質(zhì)是什么這一問題。
這個(gè)問題一直是,而且也應(yīng)該是文學(xué)批評(píng)所關(guān)注的中心問題,而答案則因?yàn)榕u(píng)家的社會(huì)或倫理觀念不同而相異,甚至因?yàn)樗麄儗?duì)文學(xué)的目的理解不同而異。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見“詩(shī)歌理論”一條,這里僅討論一些主要論點(diǎn)。
認(rèn)識(shí)性理論斷言,文學(xué)傳播知識(shí),闡述真理。這是文藝復(fù)興和新古典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老調(diào)。這類批評(píng)認(rèn)為,詩(shī)人的虛構(gòu)是為了闡述某種普遍真理的手段,揭示具體真理是歷史學(xué)家的職責(zé),而詩(shī)人的任務(wù)則是揭示普遍真理。奧古斯都時(shí)期的詩(shī)人正是利用這種觀點(diǎn),為他們拒絕講明郁金香有多少條紋的詩(shī)風(fēng)辯解。浪漫派詩(shī)人雖然反對(duì)這種不負(fù)責(zé)任的風(fēng)格,卻依然堅(jiān)持詩(shī)人貴在揭示普遍真理的理論。例如華茲華斯盛贊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詩(shī)的目的就是“揭示真理,揭示普遍真理.而不是探討個(gè)別的、具體的真理”。詩(shī)中傳遞的知識(shí)有別于生活中的、具體的知識(shí);其區(qū)別在于一方面是想象的或情感的知識(shí),另一方面是純理性的知識(shí)。雪萊的《詩(shī)之辯護(hù)》就貫穿著這種認(rèn)識(shí)。濟(jì)慈的名言“用脈搏去證明”也蘊(yùn)含了這樣的認(rèn)識(shí)。但是,文學(xué)如果是純粹認(rèn)識(shí)性的,它從原則上講與科學(xué)便毫無差別了;而傳統(tǒng)上人們又將把文學(xué)看做認(rèn)識(shí)性的觀點(diǎn)與認(rèn)為文學(xué)引起情感的觀點(diǎn)結(jié)合在一起了。象征主義理論和大部分與象征主義有關(guān)的詩(shī)歌首先系統(tǒng)地徹底否定認(rèn)識(shí)性理論。瓦萊里,特別是馬拉梅和艾略特堅(jiān)持認(rèn)為,詩(shī)歌應(yīng)該摒棄敘述、論證、說理等散文手法,而應(yīng)該像音樂一樣把自己限制于建造非寫實(shí)性的宇宙之中。與這一思潮并行發(fā)展而又顯然不同的是,人們的興趣從有意識(shí)創(chuàng)作過程轉(zhuǎn)到無意識(shí)創(chuàng)作過程,提倡詩(shī)應(yīng)該用夢(mèng)囈般的語(yǔ)言而不是理性語(yǔ)言進(jìn)行創(chuàng)作。蘭波、洛特雷阿蒙和路易斯·卡羅爾是這一思潮的先驅(qū)。他們的理論最后發(fā)展為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對(duì)于文學(xué)的理論是否是認(rèn)識(shí)性的,批評(píng)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而比這種爭(zhēng)議具有更加深遠(yuǎn)影響的是關(guān)于文學(xué)是說教性的還是審美性的爭(zhēng)論。前者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效果,后者則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本身。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是說教性的。賀拉斯的名言“愉悅和有用”便是把說教觀點(diǎn)和言情觀點(diǎn)糅合在一起的產(chǎn)物。直到18世紀(jì),這種說法還是人們普遍接受的信條。賀拉斯的理論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shè):文學(xué)的兩種目的是相互獨(dú)立互不影響的。在現(xiàn)代讀者看來,這種假設(shè)是幼稚可笑的。只有確信文學(xué)能影響讀者的態(tài)度及行為,才能主張文學(xué)可以發(fā)揮有用的社會(huì)功能,因此,所有為詩(shī)辯護(hù)者,都堅(jiān)持詩(shī)歌具有說教性的觀點(diǎn)。說教理論的弱點(diǎn)是明顯的。首先,這些理論導(dǎo)致文學(xué)可以被代替的推論:假若欣賞詩(shī)可以起到匡正人倫、改變?nèi)藗兩顟B(tài)度的作用,那么改變一下環(huán)境、上一門心理分析課程或者服用一種藥品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第二,說教理論似乎與實(shí)際的詩(shī)歌欣賞風(fēng)馬牛不相及。T·S·艾略特堅(jiān)持認(rèn)為,“詩(shī)不應(yīng)該成為哲學(xué)、神學(xué)或者宗教的代替物”;濟(jì)慈反對(duì)說教理論;杜威相信,哲學(xué)家建造美學(xué)的能力大小取決于他的體系能否抓住經(jīng)驗(yàn)的本質(zhì)。這三位互不相同的思想家所關(guān)注的問題都是相同的:評(píng)論詩(shī)歌不能歪曲其本質(zhì)。最后,持說教觀點(diǎn)的批評(píng)家們總是情不自禁地用非本質(zhì)的,嚴(yán)格地講,是用毫不相干的標(biāo)準(zhǔn)衡量一首詩(shī)。例如,約翰遜博士貶斥蒲柏的《懷不幸女士之詩(shī)》,就因?yàn)檫@首詩(shī)對(duì)一個(gè)敢于違抗父母之命的姑娘表示了同情。實(shí)際上,詩(shī)中沒有什么應(yīng)受到如此嚴(yán)厲的抨擊之處。約翰遜博士不贊成蒲柏對(duì)這個(gè)姑娘的態(tài)度,將他的不滿轉(zhuǎn)嫁到對(duì)待這首詩(shī)上,應(yīng)該受到譴責(zé)的是約翰遜。要能正確分析不同的評(píng)論,辨明什么是詩(shī)作的真正效果,從而進(jìn)一步了解說教理論的意義,這是很難的。龐德和勞倫斯等現(xiàn)代作家都曾苦苦思索過這個(gè)問題。
我們今天對(duì)理論批評(píng)提出的首要要求是,它不應(yīng)該否定“新批評(píng)”思潮的成就。對(duì)于“新批評(píng)”,評(píng)論界依然爭(zhēng)論不休,然而,不管這一思潮堅(jiān)持怎樣的目的(實(shí)用的、理論的、說教的,甚至非批評(píng)的),我們對(duì)它的最好詮釋是,它是一種批評(píng),我們應(yīng)該盡力保存和利用這種批評(píng)取得的成就。理論批評(píng)家甚至有可能像實(shí)用批評(píng)家那樣,從解釋人手;理論批評(píng)家是否這樣做取決于他是一位哲學(xué)家還是一位文學(xué)家。燕卜蓀的文章幾乎總是與具體的詩(shī)作相關(guān),總是把自己喜愛的詩(shī)作詳細(xì)討論,認(rèn)為它們理所當(dāng)然地應(yīng)該受到他人的欣賞,而且他關(guān)心的是詩(shī)中體現(xiàn)的普遍的文學(xué)和語(yǔ)義問題。另一極端的著作有科林伍德的《藝術(shù)原理》、約翰·杜威的《作為經(jīng)驗(yàn)的藝術(shù)》和理查茲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原理》。這些專著的標(biāo)題就清楚地表明了理論批評(píng)和實(shí)用批評(píng)在功能上是涇渭分明的。介乎兩個(gè)極端之間的有W·K·威姆薩特的《詞語(yǔ)偶像》和蘭塞姆的《世界的軀體》。英語(yǔ)文學(xué)批評(píng)史上每一位著名的批評(píng)家都十分關(guān)心理論問題,而對(duì)這一問題最關(guān)心的也許是柯爾律治(見其《文學(xué)傳記》第12—14章)。
文學(xué)批評(píng)將文學(xué)作為文學(xué)來研究的學(xué)問。其他一些學(xué)科也應(yīng)用同樣的題材,但是不像批評(píng)那樣,必須完全集中在現(xiàn)代讀者的反應(yīng)上,而可能為校勘、文獻(xiàn)學(xué)和其他形式的學(xué)術(shù)研究提供研究方法;或者為自己樹立其他目標(biāo)。其中主要有兩種目標(biāo),即歷史學(xué)目標(biāo)和心理學(xué)目標(biāo)。研究文學(xué)史的學(xué)者關(guān)心的是前人認(rèn)為詩(shī)歌是什么,或者在一首具體詩(shī)歌中發(fā)現(xiàn)了什么,而不是從批評(píng)家的基本假定出發(fā),認(rèn)為這首詩(shī)此時(shí)此地對(duì)他有所述說。文學(xué)心理學(xué)家關(guān)心的是一首詩(shī)與詩(shī)人個(gè)性的關(guān)系,而不注重讀者對(duì)詩(shī)的理解。毫無疑問,歷史學(xué)家、文獻(xiàn)學(xué)家和心理學(xué)家,能為批評(píng)家提供一些必要的幫助。對(duì)于一首幾百年前創(chuàng)作的詩(shī),我們就需要?dú)v史學(xué)家為我們解釋某些詞在當(dāng)時(shí)的含義然后才能充分了解這首詩(shī)的內(nèi)涵。但是文學(xué)史、傳記學(xué)和對(duì)創(chuàng)作過程的研究本身又都自成學(xué)科,它們都力求不帶個(gè)人感情色彩,而不像文學(xué)批評(píng)那樣無法擺脫主觀色彩。
二、批評(píng)的種類
人們通常視為批評(píng)種類的是批評(píng)興趣的不同模式。這些種類是在現(xiàn)實(shí)的文學(xué)研究中相互獨(dú)立發(fā)展而形成的。其中有些種類代表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橫斷面,例如,對(duì)作品和作家的評(píng)價(jià)既不完全是分析性的描述,又不完全屬于文學(xué)理論評(píng)述,因而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獨(dú)立的種類——判斷性批評(píng)。另一些批評(píng)理論來源于超越了文學(xué)范圍的哲學(xué)領(lǐng)域,如絕對(duì)主義和相對(duì)主義批評(píng)。這些不同的理論產(chǎn)生了另一系列的批評(píng)種類,也就是說,不同類屬的批評(píng)家解釋文學(xué)現(xiàn)象時(shí)總是從不同知識(shí)領(lǐng)域汲取營(yíng)養(yǎng)。現(xiàn)在公認(rèn)的大部分批評(píng)種類都屬于這后一種情況。
任何批評(píng)家探討文學(xué)現(xiàn)象時(shí),都難免或明或暗地把它們與某一種事實(shí)或者觀念框架相聯(lián)系,而他所選擇的框架對(duì)于他能取得怎樣的結(jié)果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可能選擇把自己評(píng)論的內(nèi)容限制在一些具體的文學(xué)事實(shí)和文學(xué)觀念里。例如,形式批評(píng)家就把一首詩(shī)當(dāng)做一個(gè)獨(dú)立的存在看待,把詩(shī)人僅僅當(dāng)做詩(shī)歌的創(chuàng)造者看待。另一方面,他也許會(huì)發(fā)現(xiàn)文學(xué)批評(píng)之路在于文學(xué)之外,在歷史學(xué)、人類學(xué)、心理分析或者其他有關(guān)的學(xué)科領(lǐng)域。因而他會(huì)覺得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最有意義的方法就是把文學(xué)置于這些相關(guān)學(xué)科的角度來研究。這樣就產(chǎn)生了社會(huì)學(xué)批評(píng)、心理學(xué)批評(píng)等不同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種類。
這樣籠統(tǒng)地將批評(píng)家分類未嘗不可,但如果將這些標(biāo)簽貼到每個(gè)批評(píng)家身上則顯然不能說明全部問題。雖然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某位批評(píng)家是歷史批評(píng)家或者心理批評(píng)家,但事實(shí)上沒有一位批評(píng)家純粹屬于某一類型。在實(shí)踐中,他可能會(huì)在不同的評(píng)論文章中應(yīng)用不同的理論,輪流使用形式分析理論、文學(xué)史理論、倫理學(xué)或社會(huì)學(xué)理論等等。他這樣做只是為了學(xué)術(shù)上的需要。
1.印象批評(píng)
實(shí)際上,不論是一個(gè)漫不經(jīng)心的讀者,還是一位訓(xùn)練有素的批評(píng)家,沒有一個(gè)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氣質(zhì)和個(gè)人經(jīng)歷,他的判斷必然是在個(gè)人氣質(zhì)和經(jīng)歷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但是批評(píng)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明顯地依靠自己的個(gè)人判斷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卻因人而異。有些批評(píng)家認(rèn)為,從事文學(xué)批評(píng)的首要任務(wù)就是建立起客觀的標(biāo)準(zhǔn),盡可能地?cái)[脫主觀色彩,而另一些批評(píng)家,特別是印象批評(píng)家則不以為然,他們?nèi)螒{個(gè)人興趣驅(qū)使,評(píng)論作品時(shí)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不提出任何論證。他們認(rèn)為,個(gè)人敏銳的感覺才是文學(xué)批評(píng)依賴的惟一有效條件。
印象批評(píng)家雖然也常常引用歷史等學(xué)科的知識(shí)充實(shí)自己的觀點(diǎn),但是,這一流派的名稱卻源于他們自身的批評(píng)習(xí)慣:他們總是圍繞自己的直接悟性和印象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典型的印象批評(píng)家評(píng)論一首詩(shī)時(shí),總是娓娓敘述該詩(shī)在他心中喚起的動(dòng)人感受,總是隨心所欲地探討這些感受,盡管他有時(shí)也參照詩(shī)人的其他作品,但大部分時(shí)候是在自己的文學(xué)和生活經(jīng)歷中自由馳騁。正像瓦爾特·佩特所言:“在美學(xué)批評(píng)中,認(rèn)識(shí)客體本質(zhì)的首要步驟是把握住自己印象的本質(zhì),即辨別自己的印象,認(rèn)清自己的印象。”(《文藝復(fù)興史研究》序言)佩特極少利用文學(xué)理論強(qiáng)化自己的印象,對(duì)他所討論的詩(shī)歌和詩(shī)人也不做全面描述。自覺的印象主義往往依賴舞臺(tái)布局來加強(qiáng)戲劇效果,印象批評(píng)家也同樣把他的個(gè)人印象一一加以戲劇化。其結(jié)果是他可能創(chuàng)造出第二部藝術(shù)作品來解釋第一部作品。這類批評(píng)家中的知名者有哈茲里特和蘭姆、阿納托爾·法蘭士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作為批評(píng)家,這些印象主義者難以保持平衡,他們一方面要避免墮入徹頭徹尾的自傳中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陷進(jìn)盲目追求感官享受的境地。但有些作者由于技巧不夠嫻熟而失去平衡,因此為這種批評(píng)方法敗壞了聲譽(yù),直到今天人們通常還會(huì)不屑一顧地說那不過是印象主義而已。但是這種批評(píng)的最佳作品絕非像貶損它的人所說的那樣淺薄,那樣不完全;它具有自身的連貫性,并常常具有某種獨(dú)到的啟發(fā)性,從而使讀者能夠看到新的東西,因此它作為一種富于感染力的批評(píng)仍有其一席之地。
2.技巧批評(píng)
阿納托爾·法蘭士認(rèn)為,批評(píng)應(yīng)能使靈魂在名著中體驗(yàn)到種種歷險(xiǎn),然而,當(dāng)批評(píng)期望提供超過這一要求以外的東西時(shí),它無疑需要發(fā)現(xiàn)更多的“客觀”方法。事實(shí)上,與印象批評(píng)家探討精神世界的方法相比,其他所有種類的批評(píng)提供了更易于理解的途徑,提供了某種比印象批評(píng)更正規(guī)、更易于接受的方法。每一種批評(píng)都在追求能看得見的并能用某種貫穿始終的方法描述的結(jié)果,都在探索能歸納出明確原則的結(jié)果。在所有批評(píng)種類當(dāng)中,最集中于文學(xué)角度探討詩(shī)歌的是技巧批評(píng)的各個(gè)分支。這類批評(píng)除了關(guān)注文學(xué)本身以外,對(duì)其他方面了無興趣。它們最感興趣的只有詩(shī)歌的結(jié)構(gòu)和風(fēng)格。純粹派認(rèn)為,只有這類批評(píng)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技巧批評(píng)家評(píng)論詩(shī)歌時(shí),遵循三種互不相同而又互為補(bǔ)充的方法之一:把一首詩(shī)與一種類型或一類詩(shī)相聯(lián)系;將一首詩(shī)作為一個(gè)本身完整的形式實(shí)體;或者把一首詩(shī)作為某種文體現(xiàn)象加以研究。
(1)類型批評(píng)
這實(shí)質(zhì)上是以詩(shī)的形式特征劃分詩(shī)的類型的一種方法。批評(píng)家針對(duì)作品中可能包含的因素以及可能產(chǎn)生的效果,首先建立一些比較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自維達(dá)至約翰遜博士的二百多年間,這成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基本程序。艾迪生在《旁觀者》上評(píng)論《失樂園》的文章指出,某些“種類”的詩(shī)具有獨(dú)立的特征。他們?cè)u(píng)論一部新作品時(shí)首先要問的問題可能是:“這是什么種類的詩(shī)?”如果一首詩(shī)呈現(xiàn)史詩(shī)的某些特征,那么便可以假設(shè)它必然包含某些章節(jié)和人們慣用的技巧,而且還包含著亞里士多德在悲劇中發(fā)現(xiàn)的普遍性因素(情節(jié)、人物、用詞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相互作用便產(chǎn)生出某種易于辨認(rèn)的文學(xué)模式。一旦某些成分消失或者各種因素之間失卻平衡,詩(shī)的結(jié)構(gòu)和效果將隨之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這首詩(shī)可能與史詩(shī)在一些方面相悖而成為英雄傳奇,在另一些方面相悖而成為模擬史詩(shī)或者某種非驢非馬的形式。無論如何,不了解面前的作品屬于什么種類,批評(píng)家便無法應(yīng)用適當(dāng)?shù)臉?biāo)準(zhǔn)。但是一旦確定了它的種類,就可以進(jìn)一步考察詩(shī)人是怎樣運(yùn)用這種形式的基本手法將各個(gè)組成部分納入既定主題,使之融為一體。
類型批評(píng)在18世紀(jì)衰落了。雖然當(dāng)時(shí)的批評(píng)家還沒有完全拋棄這種批評(píng)所使用的基本詞匯,但一些著名的批評(píng)家(如歌德和席勒)都在試圖重新解釋類型批評(píng)的基本原則,類型批評(píng)已不再受批評(píng)家的重視而成了文學(xué)史家研究的對(duì)象。這種批評(píng)雖然在文學(xué)史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但除了進(jìn)行區(qū)分史詩(shī)、抒情詩(shī)、戲劇詩(shī)等等對(duì)于詩(shī)歌類型的傳統(tǒng)劃分之外,在批評(píng)主流中已失去了地位。然而,今天的批評(píng)界風(fēng)行對(duì)詩(shī)的結(jié)構(gòu)作細(xì)致分析,因此,類型批評(píng)的描述功能重新引起了廣泛重視。不過,我們尚不能說它是一種獨(dú)立的批評(píng)種類,更不能說它是一種主導(dǎo)的批評(píng)類型。但類型批評(píng)如今在批評(píng)史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批評(píng)家,不論他堅(jiān)持哪種文學(xué)理論,均仍然沿用類型批評(píng)在劃分詩(shī)歌形式時(shí)所使用的標(biāo)準(zhǔn)術(shù)語(yǔ),從悲劇到五行打油詩(shī),皆是如此。批評(píng)雖然不再認(rèn)為形式是自主的,但依然認(rèn)為形式自有它的特殊性,僅這一點(diǎn)就足以證明類型批評(píng)仍有其頑強(qiáng)的生命力。
(2)形式批評(píng)
技巧批評(píng)家應(yīng)用的第二種方法是將一首詩(shī)作為一個(gè)獨(dú)特的統(tǒng)一體看待,認(rèn)為它是將各種因素以獨(dú)特的方法糅合在一起的產(chǎn)物。他有時(shí)也許發(fā)現(xiàn)將詩(shī)劃分為不同類型的做法很有用,但是他感興趣的不是劃分詩(shī)歌的類別,而是深入分析一首具體詩(shī)作中應(yīng)用的具體方法和技巧。在技巧批評(píng)家看來,一首詩(shī)的形式就像有機(jī)體的生命一樣,是個(gè)別的而不是類別的特征;因而,批評(píng)的目的便是分析一首詩(shī)的每個(gè)細(xì)節(jié)對(duì)決定其獨(dú)特形式所起的作用。20世紀(jì)文學(xué)批評(píng)發(fā)展最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就是在這一觀點(diǎn)的影響下,技巧分析的勃興。批評(píng)界接受了“有機(jī)形式”這個(gè)基本比喻,重新為形式下定義,以便使形式和“意義”發(fā)生直接的聯(lián)系。
既然構(gòu)成形式和意義的材料是詞匯,現(xiàn)代分析批評(píng)家關(guān)注的必然是一首詩(shī)中詞匯發(fā)生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他們?cè)谘芯恳皇自?shī)時(shí)致力于詳細(xì)解釋詞語(yǔ)的表面意義、比喻、象征、意象和節(jié)奏感等。在眾多的技巧批評(píng)家中,I·A·理查茲關(guān)于詩(shī)歌意義的理論著作掀起了技巧批評(píng)的浪潮,布魯克斯和華倫的《理解詩(shī)歌》一書將這種批評(píng)方法引進(jìn)到無數(shù)的美國(guó)大學(xué)課堂上;他們無疑是技巧批評(píng)的佼佼者。這種批評(píng)分析詩(shī)作時(shí),對(duì)詩(shī)本身以外的價(jià)值不屑一顧,而只分析詩(shī)作內(nèi)部的相互關(guān)系,盡可能由此分辨出詩(shī)的優(yōu)劣。技巧批評(píng)家應(yīng)用他們的方法并不能立即指出某一首詩(shī)的優(yōu)劣,也無法解釋一首詩(shī)為什么優(yōu)美而另一首僅僅不錯(cuò)。當(dāng)然在實(shí)踐中,這種方法常常和某一套獨(dú)立的道德或社會(huì)標(biāo)準(zhǔn)相關(guān)聯(lián),利維斯的著作就是如此;批評(píng)家以此將一首詩(shī)與更廣泛的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在一起。
(3)修辭批評(píng)
無論是類型批評(píng)還是現(xiàn)代的形式批評(píng)均與修辭分析有著許多相同的技術(shù)手段,也可以說,它們得益于修辭分析。修辭批評(píng)家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他們研讀詩(shī)作時(shí),尋求的是各種修辭法的漂亮例證,而將詩(shī)的整體意義拋卻腦后,傳統(tǒng)的修辭學(xué)家讀詩(shī)時(shí),也在尋找修辭手法,但絕不是因?yàn)樵?shī)的整體意義不重要才那樣做,而是因?yàn)槊恳环N手法都加強(qiáng)了整體構(gòu)造中的局部效果。從亞里士多德到昆提利安,所有古典修辭學(xué)權(quán)威都精辟地論述過從轉(zhuǎn)義、擬人到句法和音律等修辭手法。每種手法都是一種技巧,能加強(qiáng)演說效果,使演說家妙語(yǔ)連珠。修辭手法起初是演說家的一種應(yīng)用心理學(xué),后來被普遍應(yīng)用于散文和詩(shī)歌分析;即使在古典文學(xué)時(shí)期,修辭也并非僅僅局限于演說中。在中世紀(jì)和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修辭在教學(xué)中占有重要地位。盡管到17世紀(jì),修辭學(xué)被擠出了教學(xué)界,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修辭方法又成為一種重要的詩(shī)歌技巧。今天,修辭學(xué)的地位一落千丈。盡管如此,修辭手法在今天的文學(xué)描寫中仍然俯拾皆是。隱喻、對(duì)偶、擬聲等五花八門的修辭手法在I·A·理查茲和肯尼思·伯克等現(xiàn)代修辭理論家的筆下也被賦予了新的內(nèi)容。
(4)文體批評(píng)
但是,比這些修辭手法更重要的是這些手法背后的普遍觀念——文體學(xué)的觀念。古典修辭學(xué)認(rèn)為,一段話語(yǔ)不僅包含某些陳述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的先后次序,而且包含著某種表達(dá)方式——即根據(jù)主題的要求和話語(yǔ)的目的所選擇的優(yōu)雅、普通或者低下的文體。傳統(tǒng)修辭學(xué)家正是基于這一概念才支持類型理論的,因?yàn)槿藗兤毡檎J(rèn)為,像悲劇和史詩(shī)這樣的高雅文學(xué)形式與喜劇和哀歌這樣的低下文學(xué)形式之間存在著明顯差別,而這種差別與其說是存在于題材上還不如說是存在于表現(xiàn)方式上。事實(shí)上,許多關(guān)于文學(xué)類型的討論還是圍繞對(duì)文體的這種認(rèn)識(shí)展開的。但文體這一概念現(xiàn)在被無限拓展,從某種角度看,幾乎屬于文學(xué)的所有特征都可以看成是文體的特征。其結(jié)果是,文體批評(píng)不再是屬于修辭學(xué)家的財(cái)產(chǎn),而且同樣屬于印象批評(píng)學(xué)者和歷史批評(píng)學(xué)家:印象批評(píng)學(xué)者可以摒棄一切技巧分析而集中在文體批評(píng)上;而歷史批評(píng)學(xué)家常常將文體分析視為自己分內(nèi)的事。因此,批評(píng)家分析文體不僅是為了描述一首詩(shī)的語(yǔ)言特點(diǎn)(如生硬或流暢,平淡或艷麗等),也不僅是要將文學(xué)模式普遍化(如高尚、哀怨等),而且是為了確定一首詩(shī)的獨(dú)特風(fēng)格(如維吉爾式、彼特拉克式、拜倫式等),或者是為了確定某種具有民族特點(diǎn)的表現(xiàn)方式(如高盧式、日耳曼式等),或者是為了概述整個(gè)時(shí)代的藝術(shù)“精神”(如希臘化時(shí)期的風(fēng)格或巴羅克風(fēng)格)。因此文體討論有時(shí)會(huì)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偏離分析具體詩(shī)作這個(gè)方向。
文體分析學(xué)家充分利用音律分析和文體學(xué)這兩種獨(dú)立的技巧,使得他們的評(píng)論扎根于具體細(xì)節(jié)之中。盡管幾百年來,音律理論一直為語(yǔ)言學(xué)和節(jié)奏理論方面的一系列極其復(fù)雜的問題所困擾,但幸運(yùn)的是,批評(píng)家已經(jīng)能夠用各種實(shí)用的體系描寫一首詩(shī)的音律,概括某一詩(shī)人運(yùn)用音律的習(xí)慣,不僅能夠在像彌爾頓或者霍普金斯的作品這樣具有強(qiáng)烈特色的詩(shī)歌中,而且能夠在音律風(fēng)格比他們普通得多的詩(shī)作中,找到獨(dú)特的習(xí)慣用法。而這種節(jié)奏特點(diǎn)是研究詩(shī)人風(fēng)格的關(guān)鍵,并且與他的修辭技巧、他的流派特征以及他的個(gè)人氣質(zhì)密切相關(guān)。如果說音律分析是研究風(fēng)格的傳統(tǒng)手段,那么文體學(xué)則是比較新的的研究方式。文體學(xué)旨在概括某一特定時(shí)期一種語(yǔ)言的整個(gè)表現(xiàn)體系。然而,該領(lǐng)域的一些學(xué)者沖破這個(gè)范圍,悉心分析某一詩(shī)人或某一時(shí)期的語(yǔ)言風(fēng)格。他們認(rèn)為千差萬別的個(gè)人風(fēng)格均是從整個(gè)語(yǔ)言表現(xiàn)體系中所作的獨(dú)特選擇,因此可以通過具體而客觀的方式對(duì)其進(jìn)行描寫。
3.文學(xué)研究
文學(xué)研究旨在搜集和證實(shí)各種“事實(shí)”而不是評(píng)價(jià)作品和作者,是最客觀的研究。長(zhǎng)期以來,人們習(xí)慣于把文學(xué)研究與文學(xué)批評(píng)區(qū)別看待,稱前者為“做學(xué)問”。關(guān)于做學(xué)問與批評(píng)這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人們爭(zhēng)論不休,這些討論常常很實(shí)用地轉(zhuǎn)向怎樣才能訓(xùn)練批評(píng)式的學(xué)者和學(xué)者型的批評(píng)家這個(gè)問題(參見弗斯特《文學(xué)知識(shí)》、韋勒克和華倫的《文學(xué)理論》第6章和第20章、戴希斯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入門》第6章)。有些作者認(rèn)為在文字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版本學(xué)、語(yǔ)言學(xué)和文學(xué)史等方面的研究是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前提,因?yàn)楸仨毾日莆账鼈兊慕Y(jié)果才能開始對(duì)作品進(jìn)行恰當(dāng)?shù)慕忉尯驮u(píng)價(jià)。而另一些作者則認(rèn)為,這些學(xué)科本身就包含批評(píng)。這個(gè)問題之所以變得復(fù)雜,是因?yàn)檫@些學(xué)科與文學(xué)評(píng)價(jià)均有程度不同的聯(lián)系。
(1)文本校勘
這既不是判斷一首詩(shī)的優(yōu)劣,也不是闡釋它的意義,而是提供必不可少的、準(zhǔn)確文本“物證”,即綜合各種證據(jù),去偽存真,盡可能地復(fù)制出作者的原稿。但是,編輯們有時(shí)卻根據(jù)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忽視文獻(xiàn)證據(jù),武斷地對(duì)他們的材料下結(jié)論。蒲柏編輯莎士比亞的戲劇時(shí)和本特利編輯彌爾頓的《失樂園》時(shí)所采取的正是這種拙劣的做法。他們?nèi)我獯鄹脑鳎J(rèn)為它們的作者不可能寫出那樣的詞句,即使刪改的部分確實(shí)出自原作者之手,那也只能證明作者已經(jīng)才思枯竭,他們修改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護(hù)作者的聲望。但是現(xiàn)代編輯不再擅自作主。自19世紀(jì)中葉以來,編輯已普遍認(rèn)為,不該用自己的觀點(diǎn)影響文本。他們嚴(yán)格地根據(jù)一種編輯邏輯處理稿件,即盡可能地展現(xiàn)一部作品的出處及寫作日期等可以查清的歷史和流傳情況,比較各種手抄本和印刷本,辨別真?zhèn)我约傲鱾鬟^程中各個(gè)時(shí)期可能出現(xiàn)的失誤,這當(dāng)然是最客觀的判斷了。不過,客觀的證據(jù)有時(shí)會(huì)因編輯的鑒賞能力而不可避免地帶上主觀色彩。盡管兩種版本都經(jīng)過詳細(xì)考證,但仍需要判斷哪一種可能更接近于原文,或者僅僅需要決定某一版本是對(duì)原文的篡改、印刷錯(cuò)誤或?qū)ψ髡唢L(fēng)格的自由模仿。從這方面來講,最后還是要有賴于編輯在文學(xué)上的敏銳判斷力。僅就這點(diǎn)而言,編輯是一首詩(shī)的第一個(gè)批評(píng)家。
編輯如果還對(duì)文本加以注釋,以使讀者能讀懂其中的語(yǔ)言,了解其中的人名、地名和觀點(diǎn)所包含的典故,使詩(shī)作與其歷史背景完全相符,那么,他所做的每一步都滲透著他的文學(xué)鑒賞力。他雖然主要是提供有關(guān)事實(shí)的細(xì)節(jié),然而所謂“有關(guān)”的根據(jù)何在卻全由他自己決定。他必須隨時(shí)判斷一段詩(shī)文是否與從前的某個(gè)作品有關(guān),是否需要專門的知識(shí)和聯(lián)想模式才能獲得某種閱讀效果等等。既然他必須事先解釋一首詩(shī)才能進(jìn)而找出有關(guān)材料,那么在這種意義上,他的任何學(xué)術(shù)發(fā)現(xiàn),都要依賴于他作為批評(píng)家的眼光和在文學(xué)方面的閱歷了。然而,他卻通常認(rèn)為他的基本工作不是對(duì)作品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而是做了些具體的解釋性工作。
如果詩(shī)歌批評(píng)的興趣是在于系統(tǒng)地解釋詩(shī)作以外的東西,那么它的重心便從詩(shī)作本身轉(zhuǎn)移到了詩(shī)歌與其背景的關(guān)系上了。歷史批評(píng)、傳記批評(píng)、社會(huì)學(xué)批評(píng)和心理學(xué)批評(píng)等,都有各自對(duì)這種關(guān)系的明確定義以及對(duì)詩(shī)作的有關(guān)背景的研究方法。換言之,批評(píng)家有各自的標(biāo)準(zhǔn)和研究方式。雖然他們大多數(shù)都有不止一條切入批評(píng)的途徑,但是他們探討一首詩(shī)的方法都與其起源有關(guān);他們力圖解釋詩(shī)是怎樣寫成的,受了怎樣的影響才使一首詩(shī)具備了它自身的特點(diǎn)。這幾種批評(píng)的共同特點(diǎn)是,通過揭示詩(shī)的背景來說明詩(shī)本身的特點(diǎn)。他們認(rèn)為,既然詩(shī)僅僅是在部分意義上屬于非文學(xué)性的背景中的一種因素,那么,詩(shī)不僅是這種背景下的產(chǎn)物,而且也是對(duì)這種背景的表現(xiàn),因此,他們不免將詩(shī)當(dāng)做文獻(xiàn)證據(jù)看待了。他們既可以用背景解釋詩(shī),也可以用詩(shī)解釋背景。現(xiàn)代的形式批評(píng)家素來反對(duì)這種方法,認(rèn)為詩(shī)中的觀點(diǎn)和經(jīng)歷與詩(shī)外“相同”的觀點(diǎn)和經(jīng)歷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但是這種方法在韋勒克和華倫稱之為文學(xué)研究的“外部”方式中,卻是一種標(biāo)準(zhǔn)的程序。
(2)歷史批評(píng)
歷史批評(píng)家也許同意形式分析批評(píng)家的觀點(diǎn):即詩(shī)應(yīng)該以它本身的特點(diǎn)作為衡量它價(jià)值的標(biāo)準(zhǔn)。然而,在決定什么才是詩(shī)的特點(diǎn)上,他們的觀點(diǎn)迥然不同。歷史批評(píng)家認(rèn)為,詩(shī)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是在許多方面不同于現(xiàn)在條件的過去思想和經(jīng)歷條件的產(chǎn)物,因而只有密切研究過去的思想和經(jīng)歷產(chǎn)生的條件,才能使一首詩(shī)呈現(xiàn)出其全部意義。歷史批評(píng)家試圖將詩(shī)作重新置于它產(chǎn)生的時(shí)代,展現(xiàn)它當(dāng)時(shí)產(chǎn)生的條件和當(dāng)時(shí)讀者的反應(yīng),揭示它與當(dāng)時(shí)文藝思潮的聯(lián)系,總之,要盡可能地恢復(fù)這首詩(shī)在它的同代讀者心中喚起的感受。他們還試圖挖掘一首詩(shī)的本意,并堅(jiān)持認(rèn)為只有學(xué)識(shí)淵博的讀者才能理解一首詩(shī)。這種極端的觀點(diǎn)常見于歷史批評(píng)中。按照這一觀點(diǎn),批評(píng)家只有使自己能夠按照奧古斯都時(shí)期羅馬人那樣思維,而且要用拉丁文思維,才具備討論《埃涅阿斯紀(jì)》的資格。不那么嚴(yán)格的批評(píng)家認(rèn)為,讀者如果了解一首詩(shī)的歷史上的意義,便會(huì)更好地理解它,并認(rèn)為了解諸如宮廷戀愛的常規(guī)、幽默的心理因素、查理二世時(shí)代的政治風(fēng)云、弗雷澤的《金枝》的影響等各種各樣的細(xì)節(jié),都有助于今天對(duì)一首詩(shī)產(chǎn)生更清楚和更豐富的認(rèn)識(shí)。盡管這些歷史批評(píng)家清楚地知道,一個(gè)現(xiàn)代人既不能憑意愿而變成古人,也不能憑淵博的學(xué)識(shí)使自己返回過去,不過,他們還是認(rèn)為一首詩(shī)的過去隱含在它的現(xiàn)在之中,因而始終不遺余力地去研究它的過去。
但是作為歷史學(xué)家,他的任務(wù)不僅是弄清楚任何一首詩(shī)的背景,而是要把握整個(gè)文學(xué)界的背景,通過研究各種背景概括出文學(xué)發(fā)展的脈絡(luò)。著名的文學(xué)史家如德國(guó)的弗雷德里希·施萊格爾、法國(guó)的泰納和意大利的德·桑克蒂斯雖然在研究范圍、方法和興趣上截然不同,但有一點(diǎn)卻是共同的:他們不是羅列人名,敘述事件,核實(shí)日期,而是尋找事件的發(fā)展規(guī)律,揭示事件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這無疑是一件艱巨的任務(wù),因?yàn)樗麄儽仨殢募婋s的史實(shí)中隨時(shí)判斷什么屬于文學(xué),而什么不屬于文學(xué),哪些作者無足輕重,哪些影響甚大。但是這種歷史研究除了可能偶爾將文學(xué)領(lǐng)域以外的格式強(qiáng)加在文學(xué)資料上之外,當(dāng)然不能隨心所欲地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上的判斷。在文學(xué)史家看來,有些作者和作品之所以超越了當(dāng)時(shí)的背景,可能是因?yàn)樗麄儜?yīng)用了某種新的表現(xiàn)方法,或者是因?yàn)樗麄儺惓G逦乇憩F(xiàn)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生活的某個(gè)方面。文學(xué)史家認(rèn)為這類作者和作品更有意義,理所當(dāng)然地要受到他們的特別青睞。這些文學(xué)史家甚至?xí)M(jìn)一步聲言這些作者本來就非常卓越,非常偉大。文學(xué)史家作為批評(píng)家當(dāng)然有權(quán)做這種斷言,不過,他們這樣做時(shí)憑借的卻不是歷史知識(shí)。歷史證據(jù)本身能夠顯示詩(shī)和詩(shī)人因其作用而具有的價(jià)值——他們的代表性以及在歷史上產(chǎn)生的影響,但卻無法揭示詩(shī)人的自身價(jià)值和詩(shī)作的內(nèi)在價(jià)值。由于不能分清這二者的區(qū)別,而產(chǎn)生了一種傾向,認(rèn)為凡是好的作品就是有“意義”的作品,這種認(rèn)識(shí)掀起了對(duì)三流作品進(jìn)行考古式研究的浪潮,不僅加大了學(xué)者與批評(píng)家之間的距離,而且對(duì)雙方都沒有任何裨益。
文學(xué)史研究?jī)H僅是文化史和思想史領(lǐng)域中的一部分,在兩個(gè)領(lǐng)域當(dāng)中,文學(xué)史是研究證據(jù)的許多來源之一。文化史學(xué)者也許希望,也許不希望,發(fā)現(xiàn)在一個(gè)特定的時(shí)期內(nèi)所有文化性創(chuàng)造活動(dòng)之間存在著一致性。但不管怎樣,他都認(rèn)為所有這些活動(dòng)均表達(dá)了時(shí)代精神,同時(shí)又自成體系,具有自身的連續(xù)性。文化史研究中的一種叫做思想史,這種研究確實(shí)是在尋找某個(gè)特定歷史時(shí)期中的一致性,它的前提是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它獨(dú)特的時(shí)代精神,這種精神不僅體現(xiàn)于當(dāng)時(shí)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之中,而且還體現(xiàn)于當(dāng)時(shí)所有機(jī)構(gòu)之中。研究這種時(shí)代精神的史學(xué)家致力于研究一個(gè)時(shí)代的形式哲學(xué)、科學(xué)、藝術(shù)以及社會(huì)習(xí)俗的發(fā)展情況,他之所以研究文學(xué)僅僅是想把文學(xué)作為這個(gè)時(shí)代特定思想模式的證明;當(dāng)然,也可能是把文學(xué)作為對(duì)他自己關(guān)于人類文明的理論的證明。《西方的衰亡》的作者斯彭格勒就是如此。
文化史的另一個(gè)分支是由A·O·洛夫喬伊創(chuàng)立的“觀念史”研究。這個(gè)分支主要研究哲學(xué)問題,而不甚關(guān)心時(shí)代精神。這個(gè)分支旨在追溯一種哲學(xué)思想在它們漫長(zhǎng)的發(fā)展過程中,對(duì)某些哲學(xué)家的哲學(xué)體系的形成以及其他文化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有著怎樣的影響。文學(xué)是為這一歷史詳細(xì)地提供解釋性材料的主要源泉(見洛夫喬伊的《存在之鏈》第1章,該章是這種研究方法的經(jīng)典闡述)。批評(píng)家利用以上這些學(xué)科的知識(shí)進(jìn)行文學(xué)研究,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文學(xué)與其他文化活動(dòng)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更直接的原因是因?yàn)閷?duì)這些學(xué)科的了解能引起他們對(duì)詩(shī)人作品的知識(shí)含義更加注意,對(duì)這些詩(shī)作的隱含意義也更加注意,而詩(shī)作的隱含意義對(duì)于作品的整體連貫性卻至關(guān)重要。
文學(xué)史批評(píng)的另一個(gè)有關(guān)的分支是社會(huì)學(xué)批評(píng)。這一批評(píng)流派認(rèn)為,文學(xué)是社會(huì)的一種表達(dá)方式:詩(shī)人、詩(shī)作以及讀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huì)力量的影響和制約,因而對(duì)詩(shī)人創(chuàng)造的作品也必須作為一種社會(huì)現(xiàn)象進(jìn)行研究。盡管杜博斯和施塔爾夫人等許多早期的思想家都認(rèn)為文學(xué)既是社會(huì)生活的產(chǎn)物,又是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然而人們通常認(rèn)為真正系統(tǒng)地創(chuàng)立社會(huì)學(xué)批評(píng)的是法國(guó)歷史學(xué)家泰納。他用嚴(yán)謹(jǐn)?shù)目茖W(xué)方法闡釋一個(gè)民族文學(xué)的整個(gè)發(fā)展歷程,并為這一研究提出了一個(gè)著名的公式:“種族、社會(huì)背景、時(shí)機(jī)”,這三種因素被認(rèn)為是決定文學(xué)史的基本因素。三者相互結(jié)合如同化學(xué)反應(yīng)一樣,使一個(gè)特定時(shí)代必然產(chǎn)生一個(gè)特定的作者,并決定著這個(gè)作者作品的基本特征。后來的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家基本上拋棄了泰納這個(gè)嚴(yán)謹(jǐn)?shù)母爬ǎ槐A袅似渲嘘P(guān)于作家社會(huì)背景的簡(jiǎn)明概念。不過,人們還是覺得文學(xué)和其他藝術(shù)形式最終都服從于社會(huì)的總法則,至少可以說,各種藝術(shù)形式的發(fā)展歷程都可以通過分析社會(huì)環(huán)境因素而得到解釋。但是這樣做,社會(huì)學(xué)家便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超出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中心問題,因?yàn)樗麄儗⑽膶W(xué)的各個(gè)方面作為可以進(jìn)行定量分析的社會(huì)機(jī)構(gòu)來研究。他們可以將詩(shī)人視為某位個(gè)人或者視為職業(yè)作家,他們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理解,集中研究這位詩(shī)人的環(huán)境,詩(shī)人作品中出現(xiàn)的社會(huì)形象和其中隱含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與藝術(shù)活動(dòng)之間的關(guān)系等等(見鄧肯的《社會(huì)的語(yǔ)言和文學(xué)》)。與這種認(rèn)識(shí)一脈相承的許多實(shí)踐批評(píng)要么致力于研究一個(gè)詩(shī)人的特定社會(huì)環(huán)境對(duì)他作品的影響(如F·W·貝特森的《英語(yǔ)詩(shī)歌:批評(píng)導(dǎo)論》以及埃德蒙·威爾遜的許多論文),要么研究各種文學(xué)形式、文學(xué)常規(guī)和文學(xué)思潮的社會(huì)根源(如赫伯特·里德的《英語(yǔ)詩(shī)歌面面觀》)。毋庸置疑,這樣的研究必然會(huì)帶上心理傳記色彩,同時(shí)也會(huì)帶上人類學(xué)色彩。
從根本上講,這種批評(píng)并不總是描述性的和闡釋性的。將一首詩(shī)作為反映社會(huì)力量和意識(shí)形態(tài)產(chǎn)物的批評(píng)家,很可能武斷地認(rèn)為這些力量是健康的或者是有害的,是值得贊揚(yáng)的還是必須嚴(yán)厲駁斥的。他甚至還會(huì)要求作者有責(zé)任借文學(xué)形式提倡某種他的作品之外的東西,甚至為批評(píng)家自己的觀點(diǎn)搖旗吶喊。按照這種推理,托爾斯泰就會(huì)要求作者直接為基督教的大同社會(huì)獻(xiàn)身;弗農(nóng)·帕林頓就會(huì)更加推崇信奉杰弗遜主義的作者;朱利恩·本達(dá)則會(huì)大加贊賞那些超越大眾思想意識(shí)并用自己的作品反對(duì)這些思想意識(shí)的作者。這樣的要求本身并不比其他要求更過分。在20世紀(jì)各種要求藝術(shù)家必須有鮮明的思想意識(shí)的批評(píng)中,馬克思主義批評(píng)的影響最大。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歷史哲學(xué),其次才是一種政治行動(dòng)的綱領(lǐng)。它作為一種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僅僅是派生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為文學(xué)批評(píng)提供一個(gè)系統(tǒng)的方案,把他們的經(jīng)濟(jì)決定論與美學(xué)價(jià)值觀聯(lián)系起來。有的馬克思主義者認(rèn)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jià)值主要不在于評(píng)價(jià)藝術(shù)作品,而在于揭示產(chǎn)生這些藝術(shù)作品的基本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影響。馬克思主義批評(píng)家通常采用的方法兼顧兩個(gè)方面,認(rèn)為一部作品既是階級(jí)利益和作者志向的反映,同時(shí)又會(huì)為理解社會(huì)發(fā)展的真正目標(biāo)產(chǎn)生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影響。前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求作者將文藝作品當(dāng)做武器,剝?nèi)ベY產(chǎn)階級(jí)文化的偽裝,大力宣揚(yáng)共產(chǎn)主義理想,號(hào)召人們堅(jiān)信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里人人都能享有幸福和自由,因?yàn)樗麄儗[脫經(jīng)濟(jì)枷鎖的束縛。持這種觀點(diǎn)的人對(duì)于不用自己的作品宣傳這種信念的作者是不能容忍的,甚至視其為危險(xiǎn)分子,因?yàn)樗麄兊淖髌窌?huì)導(dǎo)致人們形成錯(cuò)誤的“集體心理”(布哈林)。這些原則幾乎完全將藝術(shù)品當(dāng)做政治文件看待,因而有時(shí)導(dǎo)致怪誕的結(jié)論。有一位批評(píng)家就認(rèn)為《暴風(fēng)雨》是莎士比亞對(duì)殖民主義擴(kuò)張的政治基礎(chǔ)所作的研究,而凱利班則是劇中惟一熱愛自由的人物。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批評(píng)若盡是這樣的話,那么它肯定不會(huì)在其意識(shí)形態(tài)圈子以外產(chǎn)生任何明顯的影響。拋開意識(shí)形態(tài)的爭(zhēng)論而言,許多馬克思主義批評(píng)家確實(shí)通過集中研究階級(jí)構(gòu)成、財(cái)富和社會(huì)權(quán)力分配隨著時(shí)代而演變的情形,為文學(xué)史的研究拓寬了視野。在西方,一些不為經(jīng)濟(jì)決定論辯護(hù)的批評(píng)家,也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得到有用的啟示,使他們能夠考察文學(xué)發(fā)展趨勢(shì)背后的經(jīng)濟(jì)背景。一批觀點(diǎn)迥然不同的批評(píng)家要么一貫地,要么偶然地利用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撛u(píng)論詩(shī)作。其中較著名的有克利斯托弗·考德威爾、肯尼思·伯克、威廉·燕卜蓀和D·S·薩維奇等。當(dāng)代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批評(píng)家中最有影響的是匈牙利的盧卡契。
在上述這些“起源式”批評(píng)中,詩(shī)人本身有時(shí)似乎消失在各種影響、力量和思潮形成的叢林背后。但是還有一種歷史批評(píng)——傳記批評(píng),在這種批評(píng)中詩(shī)人無疑處于舞臺(tái)的中心。圣伯夫在他的《新月曜日》一書中寫道:“我喜歡這個(gè)作品,但卻很難在把它與其作者完全隔離開的情況下評(píng)論它。”這句話包含著這樣一個(gè)假定,即詩(shī)人的生活性格,甚至他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細(xì)節(jié),都可能是理解他的作品的鑰匙,因而就成為欣賞他這一詩(shī)作的關(guān)鍵。當(dāng)然,許多文學(xué)傳記并沒有貫穿這種觀點(diǎn)。詩(shī)人的生活也許有它獨(dú)特的魅力,而與他的作品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許多學(xué)者既對(duì)詩(shī)人的生平感興趣,同時(shí)又喜歡他的作品,但并不認(rèn)為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聯(lián)系。比如說,鮑斯韋爾的《約翰遜傳》一書并未追尋約翰遜博士的生平與他的詩(shī)作之間的關(guān)系,也沒有將約翰遜的個(gè)人品質(zhì)與他的詩(shī)作價(jià)值聯(lián)系起來,而是僅僅為后輩讀者塑造了一個(gè)既是偉人也是偉大作家的形象。同樣,約翰遜自己的《詩(shī)人傳》一書也是采取將傳記內(nèi)容和批評(píng)內(nèi)容區(qū)別對(duì)待的方法。他通常是在敘述了詩(shī)人的生平之后,再專門對(duì)他的詩(shī)作進(jìn)行評(píng)論。正如大衛(wèi)·戴希斯在《文學(xué)的批評(píng)方法》一書中所說的,這種傳記既不同于那種“從詩(shī)人的心理發(fā)展過程中尋找理解和欣賞他的詩(shī)作的線索”的傳記,也不同于那種從詩(shī)作中為詩(shī)人的生平和性格尋找線索的傳記。這后兩種傳記基本是從浪漫主義文學(xué)心理學(xué)派生出來的一種形式,它們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創(chuàng)造力并且注重詩(shī)人的思考。卡萊爾便是寫作這類傳記的泰斗。在他的研究中,他為席勒、彭斯和莎士比亞等人塑造了英雄的形象,在這些論文中他們的文學(xué)作品主要是“一個(gè)人最偉大的作品,即他所經(jīng)歷的生活”當(dāng)中的一些成分而已。圣伯夫與卡萊爾是極不相同的作者,但在創(chuàng)作文學(xué)傳記方面卻極其相似。圣伯夫以詩(shī)人的性格為軸心,以豐富的史料為背景,將詩(shī)人的生平和作品糅合在一起敘述。他的《月曜日漫談》就是這種傳記批評(píng)方面膾炙人口的典范。但是,這類批評(píng)家有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危險(xiǎn),那就是他們交替使用詩(shī)人的生平以及作品互相說明,首先從詩(shī)中演繹出詩(shī)人性格,然后又用演繹出的性格去評(píng)價(jià)詩(shī)作。格奧爾格·布蘭德斯和后來的批評(píng)家根據(jù)莎士比亞的生平評(píng)論他的戲劇和十四行詩(shī)。他們的評(píng)論明顯地具有這種傾向。然而,在其他受斯蒂芬·喬治的“內(nèi)在形式”影響的許多傳記中這種傾向是隱含的,蒂利亞德寫的《彌爾頓傳》正是如此。蒂利亞德認(rèn)為,一首詩(shī)的真正主題是詩(shī)人創(chuàng)作時(shí)的心態(tài)。但不論是弗蘭克·哈里斯那種隨筆回憶錄式的,還是大衛(wèi)·馬森那種對(duì)詩(shī)人生平與時(shí)代進(jìn)行綜合研究式的,所有傳記批評(píng)都有一種基本信念,即盡管詩(shī)人的生活經(jīng)歷對(duì)他的創(chuàng)作有所影響,然而貫穿作品始終并成為其一部分的卻是詩(shī)人的性格,在評(píng)價(jià)詩(shī)歌時(shí)如果忽視詩(shī)人的性格無異于隔靴搔癢。如果一個(gè)批評(píng)家斷言《伊利昂紀(jì)》和《奧德修紀(jì)》不是出自同一詩(shī)人之手,因?yàn)橐粋€(gè)詩(shī)人不可能在兩首詩(shī)中對(duì)狗采取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那么這位批評(píng)家所寫的傳記便很難是真實(shí)可信的。而他的這一論斷恰恰清楚地說明:從作品到詩(shī)人再回到作品的批評(píng)方法,已成為一些批評(píng)家的習(xí)慣性作法。
近年來,傳記批評(píng)從心理學(xué)的研究成果中,尤其是從風(fēng)靡一時(shí)的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中受益非淺,呈現(xiàn)著勃勃生機(jī)。雖然心理批評(píng)的各種分支研究詩(shī)作的方法絕不完全是起源性或傳記性的,但是除了I·A·理查茲的著作之外,最有影響的心理批評(píng)卻是那些把詩(shī)人的性格作為研究焦點(diǎn)的著作,或是那些對(duì)揭示詩(shī)歌創(chuàng)作過程的奧秘提出某種線索的著作。那種認(rèn)為詩(shī)人是受非理性力量驅(qū)動(dòng)的觀點(diǎn)并不新鮮。柏拉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在《伊安篇》里說過類似的話。每當(dāng)人們?cè)谙蚩娝古竦钠砬笾刑岬缴衿娴撵`感之火時(shí),都有著這種含義。雖然現(xiàn)代批評(píng)家不喜歡用靈感、繆斯等術(shù)語(yǔ),他們?nèi)匀徊贿z余力地研究詩(shī)人的創(chuàng)作過程。J·L·洛斯在他著名的《通往想象力之路》中詳細(xì)分析了柯爾律治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通過梳理柯爾律治閱讀的大量書籍,力圖追尋柯爾律治想象力的綜合過程,顯示了他所運(yùn)用的原始材料及其轉(zhuǎn)化過程,不過沒有說明這種轉(zhuǎn)化的方式。C·D·阿博特也做過類似的研究。他在《創(chuàng)作中的詩(shī)人》一書中,根據(jù)詩(shī)人的構(gòu)思和草稿分析一首詩(shī)形成的各個(gè)階段。他的分析是規(guī)范的,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心理學(xué)范疇。他著重研究詩(shī)人刻意改動(dòng)的地方,而沒有觸及詩(shī)人創(chuàng)作靈感這個(gè)最初的神秘力量,因?yàn)檎缢沟俜摇に古淼略凇兑皇自?shī)的創(chuàng)作》一文中所說的,靈感是“神賜”的。但是,許多批評(píng)家接受了弗洛伊德及其門徒的學(xué)說,試圖從詩(shī)人的潛意識(shí)中尋找靈感產(chǎn)生的奧秘。因此他們轉(zhuǎn)向精神分析理論的不同流派,對(duì)詩(shī)人創(chuàng)作這個(gè)謎做出了部分回答。
弗洛伊德的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不相一致;他的繼承者又自立門派,研究的側(cè)重互不相同,致使精神分析學(xué)理論紛繁復(fù)雜。即使撇開這些分歧不談,要想澄清精神分析學(xué)與文學(xué)批評(píng)的關(guān)系也不是三言兩語(yǔ)的事情。但總的來說,精神分析學(xué)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精神包括被意識(shí)活動(dòng)排斥和壓抑的本能需要與欲望,這些本能時(shí)常尋求發(fā)泄的渠道。由于本能活動(dòng)受到意識(shí)活動(dòng)的壓抑,便以偽裝的和象征的方式出現(xiàn)——如以夢(mèng)和藝術(shù)品的方式出現(xiàn)。這樣,精神分析便與文學(xué)發(fā)生了聯(lián)系。按照這種認(rèn)識(shí),一首詩(shī)應(yīng)該被認(rèn)為是象征性地表現(xiàn)了詩(shī)人潛意識(shí)中的幻想和欲望,為我們理解詩(shī)人性格隱秘的深處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途徑。當(dāng)然,并不是所有著名的精神分析學(xué)家都在悉心研究詩(shī)人的精神生活。查爾斯·博杜安的《精神分析學(xué)與美學(xué)》是他研究比利時(shí)詩(shī)人維爾哈倫的論著。在這篇文章中,他用了相當(dāng)?shù)钠接懽x者對(duì)詩(shī)作的反應(yīng)當(dāng)中的精神因素。不過,大部分精神分析批評(píng)都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詩(shī)人神秘的下意識(shí)。歐內(nèi)斯特·瓊斯的《哈姆雷特和奧狄浦斯》可能是運(yùn)用弗洛伊德理論分析文學(xué)作品最著名的文章。瓊斯在文章中首次提出,哈姆雷特之所以在行動(dòng)上遲疑不決是因?yàn)樗袘倌盖榻Y(jié)。如果他的分析僅此而已,那么也產(chǎn)生不了巨大的影響。瓊斯進(jìn)一步指出。哈姆雷特的內(nèi)心沖突“正是莎士比亞本人內(nèi)心沖突的反映”。他分析了哈姆雷特的精神活動(dòng)后斷言,“所有男人都有戀母情結(jié),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弗洛伊德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早期性經(jīng)歷對(duì)他潛在本能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盡管許多學(xué)者都反駁過這種觀點(diǎn),但它的影響仍然是巨大而深遠(yuǎn)的。批評(píng)家對(duì)一批詩(shī)人的分析是引入注目的,他們將其突出特點(diǎn)追溯到戀母情結(jié)、對(duì)閹割的畏懼、受到壓抑的同性戀心理或者幼兒期行徑的創(chuàng)傷等。但既然弗洛伊德理論認(rèn)為性本能是人類固有的,那么為什么這些現(xiàn)象明顯地表現(xiàn)在詩(shī)人身上呢?其實(shí)這并不奇怪,只是因?yàn)樵?shī)人的精神活動(dòng)表現(xiàn)于他們的詩(shī)歌中,而他們的詩(shī)作出版后又便于批評(píng)家搜集研究罷了。弗洛伊德理論以及他關(guān)于文學(xué)與個(gè)人本能相聯(lián)系的學(xué)說的巨大影響,并不是因?yàn)檫\(yùn)用精神分析學(xué)說研究文學(xué)作品的結(jié)果。不論我們?nèi)绾慰创u(píng)家的上述分析,有一點(diǎn)是明確的,那就是,稱職的批評(píng)家在解釋直接受弗洛伊德理論或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影響的作品中,有一個(gè)可以進(jìn)一步探索的領(lǐng)域。在近幾十年間,幾乎所有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弗洛伊德理論和這一理論引起的爭(zhēng)論的影響。批評(píng)家的任務(wù)就是指出它對(duì)具體的詩(shī)作、戲劇和小說的影響。
在弗洛伊德的《圖騰和禁忌》等著作和榮格的更大量著作中,對(duì)于反復(fù)出現(xiàn)的象征模式的探索,突破了對(duì)個(gè)人經(jīng)歷的實(shí)用限制,而進(jìn)入一個(gè)更普遍的文化傳統(tǒng)領(lǐng)域。首次提出“集體無意識(shí)”這一概念的正是榮格。他認(rèn)為“集體無意識(shí)”狀態(tài)是個(gè)人精神中最原始的部分,是種族記憶的寶庫(kù)。許多批評(píng)家摒棄了榮格的其他思想,惟獨(dú)鐘愛他的“集體無意識(shí)”學(xué)說,因?yàn)檫\(yùn)用這一學(xué)說能夠充分解釋不同時(shí)代的文學(xué)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故事和主題的原因及其強(qiáng)大影響。榮格不僅強(qiáng)調(diào)原始意象和原始模式的作用,而且同時(shí)對(duì)人類學(xué)、比較宗教、古典考古學(xué)、繪畫藝術(shù)中的肖像學(xué)以及語(yǔ)言中的象征手法等等領(lǐng)域也進(jìn)行了獨(dú)立的研究。他的這些研究重點(diǎn)集中在文學(xué)中儀式性的因素和神話因素。正是這些不同來源的結(jié)合產(chǎn)生了神話學(xué)批評(píng)學(xué)派。神話學(xué)批評(píng)目前方興未艾,在批評(píng)界影響甚大。這種興趣的主要根源既是人類學(xué)又是心理學(xué)。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奠定了神話學(xué)批評(píng)的基礎(chǔ)。蘇姍·朗格的《哲學(xué)的新途徑》展現(xiàn)了這些研究的廣度。從文學(xué)批評(píng)角度來衡量,諾思羅普·弗賴伊的《批評(píng)之解剖》是到目前為止在這一領(lǐng)域最詳盡的論作。在受榮格理論直接影響的論著中,最有啟發(fā)意義的仍然是莫德·博德金的《詩(shī)的原始模型》(1934)。
除了精神分析學(xué)以外,至少還有兩種與文學(xué)批評(píng)有關(guān)的心理學(xué)流派需要簡(jiǎn)述。這兩個(gè)分支基本都不是起源式的。其中一個(gè)是實(shí)驗(yàn)心理學(xué)派。從福克納到伯克霍夫以及后來的批評(píng)家都采用一系列統(tǒng)計(jì)學(xué)技巧,利用水平測(cè)試和選擇測(cè)試手段,例如“主題知覺測(cè)試”等,以及對(duì)美學(xué)反應(yīng)的心理學(xué)研究。另一分支是格式塔心理學(xué)派。這個(gè)學(xué)派圍繞感覺過程創(chuàng)立了它的理論,認(rèn)為美學(xué)及其他研究的特點(diǎn)就是把復(fù)雜的整體當(dāng)做整體來研究,而不僅僅是對(duì)具體部分以及對(duì)各個(gè)部分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道格拉斯·N·摩根在他的一篇論文中對(duì)這兩個(gè)心理學(xué)流派在藝術(shù)研究方面的成就做了簡(jiǎn)明的總結(jié)。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覺得實(shí)驗(yàn)心理學(xué)的研究方法并不切實(shí)可行。格式塔心理學(xué)雖然在分析視覺藝術(shù)的感覺模式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它至今仍無法成功地將其研究方法轉(zhuǎn)移到文學(xué)分析上。而魯?shù)婪颉ぐ⒍骱D吩凇秳?chuàng)作時(shí)的詩(shī)人》一書中的“做詩(shī)過程的心理筆記”一章中,又轉(zhuǎn)回去研究詩(shī)人自身了。
I·A·理查茲創(chuàng)立了審美經(jīng)驗(yàn)理論,認(rèn)為審美經(jīng)驗(yàn)與審美沖動(dòng)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他的這一理論無疑對(duì)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但與本文無關(guān),在此不作討論。正如前文所述,理查茲強(qiáng)調(diào)詩(shī)中語(yǔ)言各種特性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力地推動(dòng)了注重詩(shī)歌詞語(yǔ)分析的現(xiàn)代潮流。理查茲早年曾反對(duì)詩(shī)具有認(rèn)識(shí)性和知識(shí)性功能的說法,重新激發(fā)批評(píng)界對(duì)藝術(shù)與“真理”的關(guān)系這一古老問題展開討論。理查茲將這一關(guān)系稱為“詩(shī)與科學(xué)”的關(guān)系。理查茲自1921年出版的《美學(xué)的基礎(chǔ)》后,他關(guān)于詩(shī)歌的許多觀點(diǎn)都有所改變。他最初對(duì)詩(shī)歌功能所做的實(shí)證主義闡述依然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理論中最富有成效的一種刺激。關(guān)于他的觀點(diǎn)及其影響,見蘭塞姆的《新批評(píng)》、默里·克里格的《新的詩(shī)辯家》、威姆薩特和布魯克斯的《文學(xué)理論》等。
4.比較批評(píng)
比較批評(píng)與以上討論的各種批評(píng)截然不同,它沒有鮮明的理論體系,因而與其說是靠理論獨(dú)樹一幟,不如說是靠它的研究方法。顧名思義,比較文學(xué)就是對(duì)不同的作品、作家及藝術(shù)流派進(jìn)行比較研究,由于這種比較可以從上述的任何一種觀點(diǎn)進(jìn)行,既可以從形式和風(fēng)格方面,又可以從歷史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方面比較,這種批評(píng)與其他各種批評(píng)均有關(guān)聯(lián),因而可以認(rèn)為是任何一種批評(píng)的分支。盡管如此,它也有它本身的領(lǐng)域,因?yàn)椤氨容^”這個(gè)名字就恰當(dāng)?shù)刂赋鲞@種批評(píng)跨越不同民族文學(xué)之間的界限,可以比較莎士比亞與萊辛或者洛佩·德·維加,而且跨越不同藝術(shù)之間的界限,可以比較彌爾頓與普森,莎士比亞的《奧瑟羅》與威爾第的作品,或者奧古斯都時(shí)代典雅莊重的詩(shī)與帕拉弟奧式的建筑藝術(shù)。這種比較批評(píng)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大部分還是零散的、不系統(tǒng)的,尚停留在對(duì)風(fēng)格的特點(diǎn)、對(duì)某些主題以及對(duì)不同藝術(shù)的特點(diǎn)類比進(jìn)行孤立的研究上。不過,這種批評(píng)有著進(jìn)而概括時(shí)代精神或者美學(xué)理論的自然傾向。自達(dá)·芬奇發(fā)表《比較》后,文人學(xué)者們就開始研究不同藝術(shù)和美的聯(lián)系,撰寫了幾十篇文章,論證繪畫、音樂以及其他藝術(shù)的發(fā)展與詩(shī)歌是“并行不悖”的,當(dāng)然也有文章指出,一些著名的作品并沒有追隨時(shí)代潮流,并堅(jiān)持認(rèn)為藝術(shù)各立門庭,不可混為一談(如萊辛的《拉奧孔》和巴比特的《新拉奧孔》)。從理論上講,現(xiàn)代美學(xué)在理論水平上可以說是發(fā)軔于18世紀(jì)的比較批評(píng)。
上述各類批評(píng)當(dāng)中無論哪一種,只要是對(duì)詩(shī)的價(jià)值和詩(shī)人的藝術(shù)地位做出判斷,那么它在這種程度上就成為判斷批評(píng)了。正如以上提到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批評(píng)即使在最初階段也必然是包含著某種價(jià)值判斷的。簡(jiǎn)單地說,只要認(rèn)識(shí)某種文學(xué)現(xiàn)象,就是以某種方式把它置于一定地位,哪怕是臨時(shí)性的,因此就是對(duì)它具有某種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可能尚不成熟,需要修正,但它從一開始就是依照標(biāo)準(zhǔn)的。僅僅這樣還不能算做真正的判斷批評(píng),只有根據(jù)某種普遍的標(biāo)準(zhǔn)評(píng)價(jià)詩(shī)或者詩(shī)人的優(yōu)劣才能夠做真正的判斷批評(píng)。雖然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千差萬別,似乎毫無共同之處,但還是可以分成幾種類型。每一種批評(píng)都有它自己合適的范疇,其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和意識(shí)形態(tài)標(biāo)準(zhǔn)也不盡相同。致力于對(duì)詩(shī)作本身特點(diǎn)進(jìn)行研究的批評(píng)家所做的價(jià)值判斷基本是美學(xué)方面的,集中于作品的內(nèi)在本質(zhì)以及它獨(dú)特的心理效果。上述關(guān)于現(xiàn)代技巧分析部分講的便是如此。這類批評(píng)家在實(shí)踐中也許會(huì)應(yīng)用其他標(biāo)準(zhǔn),但主要運(yùn)用形式分析和心理價(jià)值判斷兩種方法。另一方面,凡是認(rèn)為一首詩(shī)的主要意義在于它對(duì)經(jīng)驗(yàn)做了評(píng)述的批評(píng)家,首先是用政治、社會(huì)、倫理、宗教等意識(shí)形態(tài)標(biāo)準(zhǔn)判斷詩(shī)的價(jià)值,因?yàn)榘呀?jīng)驗(yàn)作為整體來判斷時(shí),這些標(biāo)準(zhǔn)便是至關(guān)重要的。根據(jù)某一種社會(huì)或宗教觀念建立起來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則是意識(shí)形態(tài)批評(píng)的極端例子。這種批評(píng)認(rèn)為詩(shī)中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內(nèi)涵便是一切,而它是一首詩(shī)這一事實(shí)卻意義不大或者無關(guān)緊要。當(dāng)然在實(shí)踐中,絕大多數(shù)強(qiáng)調(diào)意識(shí)形態(tài)重要性的批評(píng)家并不是如此嚴(yán)守教條,并不要求詩(shī)作必須符合批評(píng)家自己的觀點(diǎn),也不要求詩(shī)作必須為某種事業(yè)服務(wù)。這類批評(píng)的核心主張非常簡(jiǎn)單,那就是,文學(xué)的大部分價(jià)值來源于一種對(duì)其他經(jīng)驗(yàn)的復(fù)雜而嚴(yán)肅的關(guān)系,而在鑒賞詩(shī)作時(shí)批評(píng)家就需要考察這是一種怎樣的關(guān)系,它的內(nèi)涵是什么,有什么啟示等等。
在文藝批評(píng)的悠久傳統(tǒng)中,意識(shí)形態(tài)標(biāo)準(zhǔn)中的倫理價(jià)值從一開始就占據(jù)了相當(dāng)?shù)牡匚弧W詮陌乩瓐D將除了贊美上帝和歌頌英雄的詩(shī)作以外的所有詩(shī)歌逐出他的理想國(guó)后,詩(shī)歌具有“匡正人倫,教育感化”作用的觀點(diǎn)便成了文學(xué)批評(píng)中的熱門話題。賀拉斯針對(duì)詩(shī)歌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和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的關(guān)系問題提出了一個(gè)著名的模棱兩可的論斷:詩(shī)歌的目的“要么是感化,要么是愉悅,抑或兼而有之”。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批評(píng)家既反對(duì)詩(shī)歌庸俗化又反對(duì)詩(shī)歌哲學(xué)化的傾向,而認(rèn)為詩(shī)歌應(yīng)通過表現(xiàn)高尚行為之美而激勵(lì)人們樹立良好的道德風(fēng)尚。這絕不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變通。早期類型批評(píng)理論的座右銘就是每一種體裁的詩(shī)歌都以它特有的方式發(fā)揮著道德感化作用。拉潘和勒博敘,維吉爾和斯賓塞,都認(rèn)為史詩(shī)具有倫理寓意,甚至政治智慧。詩(shī)歌具有道德訓(xùn)誡作用的觀點(diǎn)和“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觀點(diǎn)是詩(shī)歌批評(píng)的兩個(gè)極端,處于二者之間的觀點(diǎn)數(shù)不勝數(shù)。因此,不同意托爾斯泰的文藝觀絕不意味著就是贊同王爾德的文藝觀。
文學(xué)表現(xiàn)人在具有嚴(yán)肅的道德意義的環(huán)境中所呈現(xiàn)的性格和行為。因而,用阿諾德的話說,文學(xué)就是對(duì)生活的批評(píng)。一旦批評(píng)家認(rèn)為詩(shī)的首要功能是用道德感化的方式處理經(jīng)驗(yàn),懲惡揚(yáng)善,或者刻意塑造善的形象,或者說,一旦他必須判斷一首詩(shī)對(duì)生活的反映是正確或者錯(cuò)誤的時(shí)候,倫理批評(píng)家就粉墨登場(chǎng)了。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爭(zhēng)論和異議,因?yàn)榧词箍梢院?jiǎn)單地把藝術(shù)定義為對(duì)生活的反映,但它畢竟與它力圖表現(xiàn)的生活不是一回事,這樣,判斷藝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就不僅要包括符合生活的一面,而且必須包括遠(yuǎn)離生活的那一面。T·S·艾略特在《宗教與文學(xué)》中清楚地闡明了這個(gè)道理。他寫道:“盡管我們必須牢記,作品是否具有文學(xué)價(jià)值必須用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衡量,但作品是否偉大卻不能僅僅用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做出判斷。”雖然在總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批評(píng)之中,典型的倫理批評(píng)試圖解決文學(xué)中真實(shí)與偉大的問題,但是僅僅憑借美學(xué)或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卻不能如愿以償。
批評(píng)家應(yīng)用他們的判斷時(shí),常常忽視其價(jià)值所具備的哲學(xué)意義。但長(zhǎng)期以來,理論界爭(zhēng)論不休,試圖澄清這些價(jià)值的本質(zhì)以及它們進(jìn)入經(jīng)驗(yàn)的方式,批評(píng)家通常也以含蓄的方式參與這類爭(zhēng)論。批評(píng)家非常自信地認(rèn)為,他們?cè)谠?shī)中發(fā)現(xiàn)的這些價(jià)值是永恒的還是暫時(shí)的,可以隨著條件變化而變化。持第一種觀點(diǎn)的就是絕對(duì)主義批評(píng)家,而持第二種觀點(diǎn)的是相對(duì)主義批評(píng)家。前者認(rèn)為世間萬物都遵循一種普遍的規(guī)律,因此不論這些價(jià)值是以怎樣的形式出現(xiàn),都符合一個(gè)總的價(jià)值體系。他們還認(rèn)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的差異不過是個(gè)人或者一個(gè)時(shí)代探討真理的能力差異的反映。今天絕對(duì)主義觀點(diǎn)已不再時(shí)髦。“相對(duì)主義”這個(gè)詞有多種涵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個(gè)人相對(duì)主義”和“歷史相對(duì)主義”,二者雖然均接受心理學(xué)而不是本體論對(duì)價(jià)值下的定義,但其含義及批評(píng)方法卻不盡一致。個(gè)人相對(duì)主義認(rèn)為所有的價(jià)值都是主觀的,因此價(jià)值可以因人而異,任何個(gè)人的感知都不能認(rèn)為是絕對(duì)的、地道的印象。批評(píng)家大概會(huì)接受上述觀點(diǎn),盡管他仍可以相信他自己確認(rèn)的價(jià)值是銘刻在事物的天性之中而不可磨滅的。歷史相對(duì)主義拋棄了個(gè)人相對(duì)主義中的絕對(duì)主觀性成分,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與教育對(duì)個(gè)人的影響。它認(rèn)為,價(jià)值觀念隨著時(shí)代和風(fēng)尚的變化而變化,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或者一個(gè)民族有意義的價(jià)值,也許在另一個(gè)時(shí)代或另一個(gè)民族看來一文不值。因此在評(píng)價(jià)任何詩(shī)人的作品時(shí),都必須同時(shí)考察詩(shī)人所處時(shí)代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弗雷得里克·A·波特爾在《詩(shī)的習(xí)用語(yǔ)言》中對(duì)這個(gè)問題做了精辟的論述。
5.科學(xué)批評(píng)
最后一種需要評(píng)述的批評(píng)類型是科學(xué)批評(píng)。是否確有所謂“科學(xué)批評(píng)”完全取決于如何給這個(gè)術(shù)語(yǔ)下定義。盡管批評(píng)界有時(shí)給各種不同的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和人類學(xué)研究以及語(yǔ)言學(xué)批評(píng)、文本校勘、手稿考證,甚至傳記等冠以科學(xué)批評(píng)這個(gè)名稱,但是這些批評(píng)方法無一具備構(gòu)成一門科學(xué)的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將上述研究稱做“科學(xué)”的大多數(shù)作者不過認(rèn)為,它們對(duì)以經(jīng)驗(yàn)為依據(jù)的事實(shí)表現(xiàn)出高度的尊重,并且在描述中力求清晰與連貫。如果這是科學(xué),那么就應(yīng)該像批評(píng)家有時(shí)提議的那樣,讓文學(xué)批評(píng)也應(yīng)該朝著完全成為一門科學(xué)的方向發(fā)展。但實(shí)際上.一種研究要成為科學(xué),它所處理的材料以及材料之間的關(guān)系必須能夠經(jīng)得起經(jīng)驗(yàn)驗(yàn)證,并能從中歸納出規(guī)律,人們運(yùn)用這些規(guī)律能夠預(yù)測(cè)它的發(fā)展變化。文學(xué)作品(包括詩(shī)歌)的價(jià)值不同于音素、水位和心率,不能用科學(xué)的方法測(cè)量。文學(xué)作品的價(jià)值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盡管我們可以說發(fā)現(xiàn)了什么價(jià)值,也可以討論這些價(jià)值,但卻不能用科學(xué)的方式來確定。例如,不能僅僅根據(jù)數(shù)字統(tǒng)計(jì)結(jié)果來說明濟(jì)慈詩(shī)歌的藝術(shù)價(jià)值高于或低于拜倫詩(shī)歌的藝術(shù)價(jià)值。因此,從嚴(yán)格的意義上講,在文學(xué)(詩(shī)歌)批評(píng)領(lǐng)域,不可能有所謂的“科學(xué)批評(píng)”。以定量、定性分析為基礎(chǔ)的科學(xué)所研究的對(duì)象不是文學(xué);科學(xué)在文學(xué)研究中的作用僅是輔助性的,主要體現(xiàn)在資料收集、整理與統(tǒng)計(j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