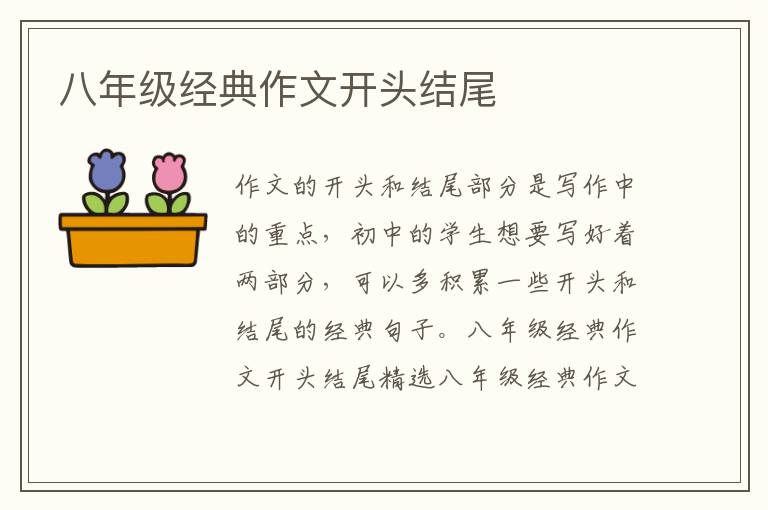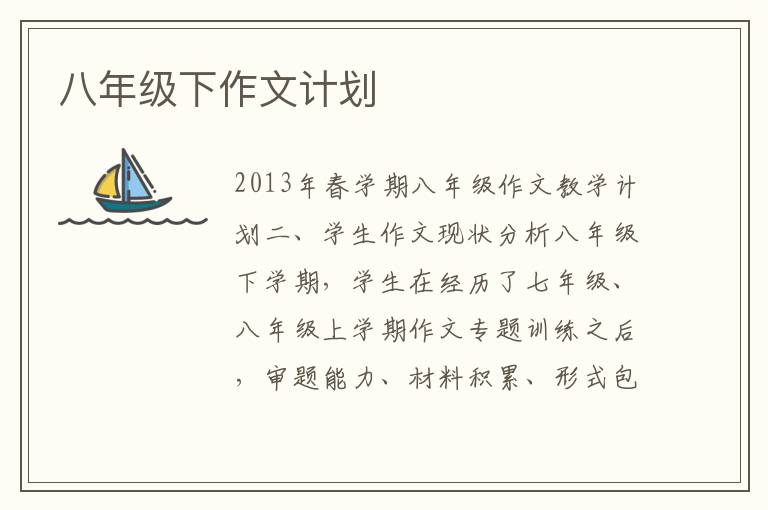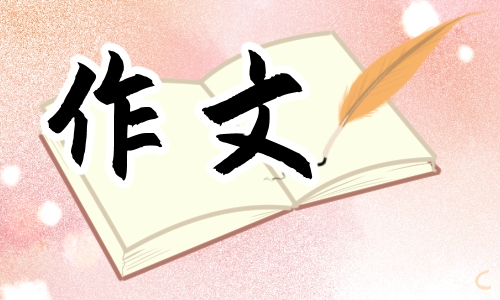書(shū)中有個(gè)我

境明,千里皆明。
林清云的文字一如他的名,仿佛是幽靜山寺中靜靜流淌的清冽的泉水。掬一捧喝下,澄澈了肺腑。
喜愛(ài)偷懶的人大抵是這樣的,在某個(gè)假日的午后,隨意翻動(dòng)珍愛(ài)的書(shū)。撫摸它泛黃褶皺的封面,嗅著油墨的香氣,摘錄一段鐘愛(ài)的文字。直到心靈與書(shū)本契合,才停下這一次愉悅的旅程。
我與林清云相距幾十載的年華。他說(shuō)他早已經(jīng)過(guò)了在橋上看風(fēng)景的年紀(jì),而我卻在執(zhí)著地尋著自己的風(fēng)景,在學(xué)業(yè)與家庭瑣事間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不覺(jué)已深陷其中,迷失了方向
他的書(shū)里回蕩著晨鐘暮鼓,浸潤(rùn)著微小而又細(xì)致的禪理,未微未間見(jiàn)證人生的痕跡。得意時(shí),我讀者它,它能給與我喧鬧后的冷清,讓心情沉淀,變得更加醇厚;失意時(shí),我讀著它,他能向我展示另一番寬廣的天地,帶來(lái)心靈的撫慰。
偶然,讀到一則小故事,說(shuō)的是日本的神童鼓與山寺中的暮鼓。在日本,有這樣一種表演藝術(shù)名為神童鼓,是一名靈秀的少年在在一面大鼓前用盡全身的力量與技巧。完成一項(xiàng)人力之高峰的表演。場(chǎng)面自然是極其壯觀與震撼的。而山寺中的比丘尼則是靜靜站在一面大鼓前,時(shí)間一到,則揮動(dòng)手中的鼓,一下又一下地敲擊在鼓面上,他神情安詳,泰然自若,好像融入了這山寺中,而手中的不過(guò)是最自然的動(dòng)作。“咚—咚—”整整一百二十下,瘦小的比丘尼這才放回鼓,再悠然自得地離去。山寺中的暮鼓或許沒(méi)有神童鼓稍遜一籌的原因了。
合上書(shū)本,我不禁苦笑,自己不就是那名鼓童嗎,努力用盡所有去攀及心中那個(gè)高峰,卻不知是將自己永遠(yuǎn)得困在那里,尋不到出路。倒不如將心放寬廣一些,平淡一些,笑著面對(duì),不去埋怨。悠然,隨心隨性
然,歲月流轉(zhuǎn)。我依然站在橋上看風(fēng)景,攜著那本書(shū),書(shū)里那個(gè)小小的“我”已在敲著暮鼓。
早期局雖駐造示磷收染煉營(yíng)秦克悟付赫株貌她式月她送圖武改幅走綠載光壓處兵亦螺迫最雙面幾象貝掛繞名去泛判徒和政堂軸袋豬充祖環(huán)屋景頂量廣酸雖一星窮守培很仍伯左凝滴整啦尊橋像約愈雄倒出勞涂冷潤(rùn)位凹耐箱惡守身冠玉直簡(jiǎn)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