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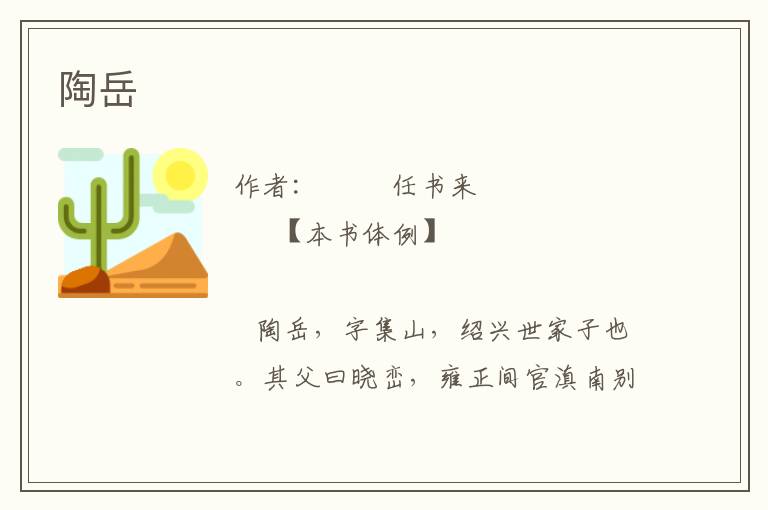
作者: 任書來 【本書體例】
陶岳,字集山,紹興世家子也。其父曰曉巒,雍正間官滇南別駕。以詿(guà掛)誤罷任,貧不能歸,遂留滇省,辦刑名有聲,大位爭(zhēng)延致之。后在永昌府幕,見書室前花盆中,有拳石焉,色深紫而光瑩射,異而詢之。其從者為本處人,答言此石不僅紫色一種,尚有大紅、銀紅、淡紫、黃、白諸色,其佳者置諸盆盎間,以為玩具,府屬各縣山中皆有之,非貴重物也。曉巒愛之甚,遂致書交好,令羅致之,共得兩巨篋。然雜色多,而大紅則僅十之二三。歸時(shí)馱以兩騾。自永昌以致鎮(zhèn)遠(yuǎn),計(jì)旱路四千余里,所費(fèi)不貲。至紹興舉以贈(zèng)人,人視之與宣石等,亦無有見重者。
后曉巒卒,集山困于諸生。家貧甚,訓(xùn)蒙以糊口。紹興珠寶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隆甲戌冬,集山偶過其地,見店中有以碧霞髓交易者。集山向聞其名而未之見也,因入視之,其物大如酒碗,色淺紅,光華自內(nèi)出,閃爍照人,與其父滇省攜歸之石絕相類,遂坐其旁以觀之。店主還價(jià)增至八十金,賣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問之,店主言:“此石鋸開可得帶版四塊,然人工寶砂之值,須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價(jià)重,買者甚稀,售完當(dāng)以一年計(jì),工本月利逐項(xiàng)算入,則所獲無幾。本地貨本難銷,且無工匠,將來當(dāng)攜至蘇揚(yáng)囫圇售之,羨余不過一分錢而止耳。”問其物以何為貴,答以大紅最上,銀紅次之,雜色又次之。
集山亟歸,取其所存者驗(yàn)之,與店中所見者無別。因檢點(diǎn)故篋,其一猶未開動(dòng),其一則所剩無幾。于是遍索室中,復(fù)得大小十?dāng)?shù)塊。集山大喜,檢大紅色小如錢者一枚,售于千秋巷別一珠寶店內(nèi),得銀百余金,作舟車之費(fèi),陸續(xù)至蘇、杭、揚(yáng)州、南京、漢口、廣州諸處售之。集山善于經(jīng)營,即于彼處買貨而返。時(shí)碧霞髓價(jià)日增一日,篋中物去未及半,計(jì)所獲已萬余金。以之買房屋,置田產(chǎn),頗稱溫飽。后逐漸售完,遂成紹興巨室云。
集山之業(yè)師曹仰堯,余舊識(shí)也。丙戌冬日相遇于梧州,坐間有談及碧霞髓者,曹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諸客。
(選自《聽雨軒筆記》)
陶岳,字集山,紹興世家子弟。父親名曉巒,雍正年間在滇南任過“別駕”之職,因受牽連被罷官。無錢回鄉(xiāng),留在云南作刑名師爺,因辦案有名,高官們爭(zhēng)相邀請(qǐng)他。后來在永昌府作幕僚,見到書房前花盆中,有一塊小石頭,深紫色,并且光彩閃射,覺得很奇異,便向入打問。跟隨他的人是本地人,回答說:“這類石頭不單是紫色一種,還有大紅、銀紅、淡紫、黃、白好幾種顏色。其中最好的可放在盆盎之中作為玩具。這種石頭永昌府所轄各縣山中都有,不是什么貴重東西。曉巒非常喜愛這種石頭,就寫信給朋友,請(qǐng)他們代為搜集,一共得兩大箱。不過,雜色的較多,而大紅的僅十分之二三。回鄉(xiāng)時(shí)用兩個(gè)騾子馱著。從永昌到貴州鎮(zhèn)遠(yuǎn)上船,光旱路就有四千多里,為此化了很多盤纏。回到紹興曾拿了些送人,可他們把此石看成與宣石差不多,沒有人看重。
后來曉巒去世,集山只中了個(gè)秀才,再也考不中舉人,家里非常窮,靠給別人家的孩子作啟蒙老師掙口飯吃。紹興的珠寶店在城中的千秋巷,乾隆甲戌年(1754)冬天,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集山從這里過,看見店中有作碧髓買賣的。集山早就聽說過“碧霞髓”這名字而沒有見過,于是就到店里去看。見這東西有酒碗大小,淺紅色,從內(nèi)向外放射出光芒,閃爍照人,和他父親從云南帶回的石頭非常象,便坐在一旁觀看起來。直到店主提價(jià)到八十兩銀子,賣者才成交而去。集山后來慢慢向店主打問,店主回答說:“這種石頭鋸開可得到四塊帶版,然而加工所需人工、寶砂得化費(fèi)三、四十兩銀子,才能制成器物。眼下這種東西價(jià)高,買者少,賣出去得一年時(shí)間,工本月利都算進(jìn)去,就賺不了幾個(gè)錢了。在本地,貨本來就難銷,又無工匠,將來應(yīng)當(dāng)帶到蘇州、揚(yáng)州原物出售,只不過能賺一分錢罷了。”問他這種石頭以哪種最珍貴,回答最珍貴的是大紅色的,其次是銀紅的,再次是雜色的。
集山匆匆回到家里,取出所存的石頭檢驗(yàn),看到和店中見的沒有什么差別。于是他就開始查點(diǎn)原來裝石頭的箱子,發(fā)現(xiàn)其中一箱還原封沒動(dòng),另一箱已所剩無幾。這時(shí)他把屋里搜尋了個(gè)遍,又得到大小十來塊。集山非常高興,檢了一枚銅錢大小的大紅色的,賣給千秋巷另一家珠寶店,得了一百多兩銀子,作為路費(fèi),陸續(xù)運(yùn)他的碧霞髓到蘇州、杭州、揚(yáng)州、南京、漢口、廣州等地去賣。集山善于經(jīng)營,又從上述各地販貨回來賣。當(dāng)時(shí)碧霞髓的價(jià)錢天天上漲,箱子里的賣出還不到一半,算了一下,已得到一萬多兩銀子。他用這錢買房屋、田地,過上了溫飽日子。后來,逐漸把所存全部賣出,便成了紹興的大戶人家。
集山受業(yè)的老師曹仰堯,是我的舊相識(shí)。丙戌冬天在梧中相遇,一群客人坐在一起閑聊,其中一個(gè)談到碧霞髓,曹因此給眾客人們講述了上述集山的故事。
本篇自始至終圍繞著“碧霞髓”這種石頭作文章。前半部分主要寫集山的父親在云南見到這種石頭,愛上這種石頭,托人搜集這種石頭,不怕路途遙遠(yuǎn)艱難運(yùn)回這種石頭。后半部分主要寫集山在困境中發(fā)現(xiàn)這種石頭的價(jià)值,逐漸售出這種石頭,遂成為紹興巨室。前后雖然寫的是不同人事,但因有碧霞髓貫徹始終,所以文章仍是一個(gè)統(tǒng)一的整體,并不顯得松散。
本篇所寫的主要人物是集山。乾隆甲戌(1754)冬,集山偶過紹興城中珠寶店的所在地千秋巷,見店中有賣自己“向聞其名而未之見也”的碧霞髓的人,好奇心驅(qū)使他進(jìn)店“視之”;當(dāng)看到這碧霞髓與父親從“滇省攜歸之石絕相類”時(shí),切身利益吸引他要弄個(gè)究竟,“遂坐其旁以觀之”;當(dāng)親眼目睹這小小的石頭待“店主還價(jià)增至八十金,賣者始肯成交而去”時(shí),集山馬上意識(shí)到自家所存的碧霞髓可能會(huì)給自己帶來一筆可觀的財(cái)富,以改變自己目前的困頓境況,于是便策略地向店主“徐問之”——借助行家弄清自家貨物的等次、用途和市場(chǎng)上這種貨物的價(jià)錢、銷售情況。從上述可以看出,集山頗有生意人的頭腦,既重視“知己”——弄清自家貨物的情況;又重視并善于“知彼”——搜集了解市場(chǎng)信息。經(jīng)營也象打仗一樣,知己知彼,方能取勝。
集山掌握市場(chǎng)情況以后,便開始他的經(jīng)營活動(dòng):先“檢大紅小如錢者一枚”,到千秋巷“別”一家珠寶店賣得車船盤費(fèi),然后根據(jù)店主提供的市場(chǎng)信息陸續(xù)把自家的碧霞髓運(yùn)到更能賺錢的蘇州、杭州、揚(yáng)州、南京、漢口、廣州等地去賣。賣掉碧霞髓不是空著返回,而是“于彼處買貨而返”,從中又賺一筆。作者評(píng)價(jià)說:“集山善于經(jīng)營。”的確一點(diǎn)不假。
集山正是靠著他的有心計(jì)、善經(jīng)營,才從以前“困于諸生”、“家貧甚”發(fā)達(dá)到后來的“遂成紹興巨室”。這固然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huì)末期沿海一帶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在當(dāng)今時(shí)代,難道我們不能從集山這個(gè)人物身上得到一些啟發(f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