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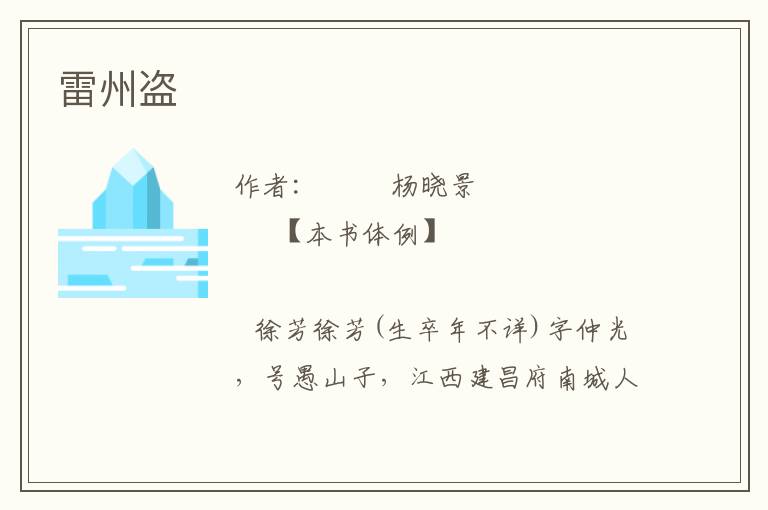
作者: 楊曉景 【本書體例】
徐芳
徐芳(生卒年不詳)字仲光,號愚山子,江西建昌府南城人。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曾任山西澤州知州。明亡,與友人鄧適彬隱居山林,入清不仕。徐芳是具有較高造詣的詩文作家,他的著作有《諾皋廣記》、《懸榻編》、《松明閣詩選》等。《諾皋廣記》是一部筆記體文言小說集,成書于順治、康熙年間,文字洗煉,富于表現力,但議論較多。
雷于粵為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殘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眾中一最黠者為偽守,持牒往,而群詭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僚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只履,否則,雖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
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辯也。守窘,擬起為變,而伏甲發,就坐捽(zuó昨)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
東陵生聞而嘆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資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選自《諾皋廣記》)
雷州是廣東最遠的郡縣。明崇禎初年,金陵有一人從京里出任雷州府太守。他乘船駛到江中,遇到了強盜。強盜問清他是雷州府新任太守,就殺了他,同時也殺了太守的隨從,只留下太守的妻子和女兒。強盜讓他們中間最狡猾的一個冒充假太守,帶著任命書前往雷州,其它強盜作為仆人跟從。誰也沒看出他們是強盜。假太守到雷州一個多月,辦事廉潔精干,把雷州治理得井然有序,成績顯著。百姓互相慶賀,認為雷州得到一位賢能的太守。同僚及負責監察地方政府的官員,也都稱頌推許他。不久,假太守發布命令,禁止外地的游客進入雷州,在他管轄的地區不許接納一個金陵人;否則,即使是太守的至親好友也同樣治罪。于是雷州人更加信服新太守,都沒想到新太守竟如此嚴格不徇私情。
沒多久,太守的兒子來了。他進入雷州境內,無人敢留他住宿。他問當地人是什么原因,才知道這是新太守發布的命令。他心里很疑惑此事。第二天早上假太守出來,太守的兒子在路邊看到此人不是他父親,上前詢問假太守的姓名及老家,都和他父親一樣。太守的兒子仔細想了想,忽然明白了,“哦,是強盜!”當時他不敢突然說出來,私下把這事告訴了監使司。監使司說:“算了,明天我請太守來吃飯,到時候你再出來。”于是監使司命令部下,讓士兵包圍太守住的地方,吃飯的地方也埋伏下甲兵。第二天,太守進來拜見;監使司讓太守飲酒,并喚出其子當面對質,假太守不認得。假太守看處境十分危急,則準備起身動手,埋伏在客廳中的武士突然沖了出來,在座位上揪住他。那些包圍假太守住宅的士兵也跟著沖進去。跟隨假太守的強盜馬上起來應斗廝殺,趁機逃掉,最后只抓住其中的七個。監使司按照法律對被抓獲的強盜進行審訊,然后給他們帶上腳鐐手銬,押解到金陵殺掉了。直到這時,雷州人才知道新太守是個強盜,而不是真正的太守。
東陵生聽過這件事后,慨嘆地說:“太不一般了!一個強盜竟能做太守,并且取得這樣大的政績!如今的太守并非強盜,然而他們的所做所為,沒有多少不象強盜的,還真不如讓強盜來當太守呢。賊做太守,他本身是強盜,可他做太守卻很賢明,且比其他太守還要好。”有人反對說:“強盜并非賢明,他只是想尋找合適時機,搜刮本地的寶物和百姓的錢財后再逃走。”東陵生接著說:“這種情況是有的,可如今的太守,哪一個不是搜刮當地的寶物和錢財后而走掉的呢?”愚山子說:“東陵生說的話太過分了!然而仔細推敲他的意思,也足以供做太守的人借鑒呀。”
徐芳的這篇筆記體小說從藝術上看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盡管作者是當時較有名氣的詩文作家,而且在本篇中也顯示了他作品結構嚴謹,層次分明,語言簡潔樸實。但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上講,卻存在相當大的缺陷。這可從兩個角度來說明:從人物塑造的角度講,作者的本意在于寫出一個比一般官員都好的“強盜”,而且他也的確寫了這位“強盜”太守“甚廉干,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但在第二層文字中,卻又詳盡地敘述監使司捉偽太守的過程,其細致程度及文字數量均大大超過了上面對偽太守的稱贊,這無疑嚴重損害了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從主題意旨的表達來看,作者記敘這件事的目的是引出最后一段,即盜與守相對比的議論文字,但第二層的文字對于這段議論的產生非但是可有可無,而且沖淡了這種對比的效果,因而成為明顯的敗筆。
但這些缺陷都不能掩蓋這篇作品的重要性,那就是作者將強盜與封建官僚所作的鮮明對比,作者借寫盜守的廉干,備受百姓歡迎,曲折地暴露了現實政治之腐敗,并在作品的結尾進一步點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猶愈他守也。”當他設想有人會用“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來反駁他時,干脆說:“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資而逸者哉?”應該說作者的這種認識與感慨是有時代感的。盡管中國歷來有成者王侯敗者賊的古訓,而且元末也有過“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的散曲流行,但在明未這種情形更為突出。徐芳的這篇作品,雖可能寫于清代的順治、康熙年間,但他記述的事實和產生感慨的社會基礎應是晚明時期,而晚明官場之黑暗,官僚對百姓的公開掠奪是相當嚴重的。在凌蒙初的“二拍”中,就寫了許多官吏誣良為盜而掠其財寶的內容,在“二刻”卷二十中還曾引了這樣一首詩:“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共一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與徐芳幾乎同時的小說批評家金圣嘆,對此也有同感,他在《水滸傳》第十八回批語中說:“官是賊,賊是老爺。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很顯然,官賊難分是明代后期的突出特點,《雷州盜》在這一點上是反映了時代的本質特征的,尤為可貴的是,本篇已不象凌蒙初那樣寫“官人與賊不爭多,”也不象金圣嘆那樣寫官與賊的“二而一,”而是將其顛倒過來,寫“賊”勝于官,這就更能顯示出該作品的思想價值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