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波,阿爾圖爾作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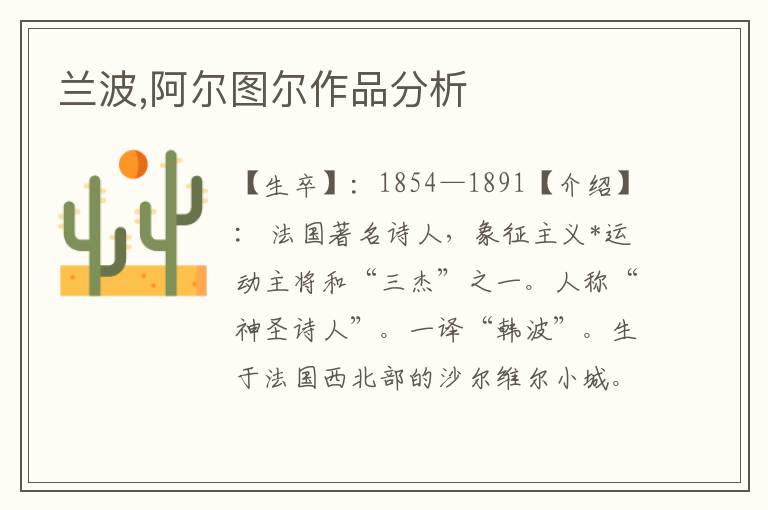
【介紹】:
法國著名詩人,象征主義*運(yùn)動主將和“三杰”之一。人稱“神圣詩人”。一譯“韓波”。生于法國西北部的沙爾維爾小城。父親是步兵上尉,母親主持家務(wù)。由于父母不和和生活困難,所以童年時期的蘭波孤僻沉悶而郁郁寡歡。蘭波從小聰穎過人。十歲時,就能熟練地用法文書寫,十五歲以拉丁文詩作震驚全校,其中一首還得到科學(xué)院頒發(fā)的頭獎。1870年,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進(jìn)入旺盛期。這一年,十六歲的蘭波進(jìn)入沙爾維爾中學(xué)文科班。一個叫伊桑巴爾的老師,十分欣賞他的才華,鼓勵他寫詩。這正是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和法國第二帝國垮臺的一年。蘭波這一年的詩作,現(xiàn)存二十二首。這些詩作歌頌了法國大革命中的起義者,表現(xiàn)了對于窮苦人的同情和對于教會與戰(zhàn)爭的抗議,詩中也流露出對遠(yuǎn)游的渴望,創(chuàng)作方法基本上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1871年初,蘭波曾去巴黎,在那里呆了半個多月,于公社起義一周前返回故鄉(xiāng)。蘭波雖然未參加過巴黎公社的起義戰(zhàn)斗,但對公社革命是理解和擁護(hù)的。他寫了一些歌頌巴黎公社的詩篇,如《巴黎的狂歡》、《巴黎戰(zhàn)爭的歌》等,歌頌公社革命賦予巴黎以“最崇高的詩意”,痛斥凡爾賽的劊子手是“青灰色的蛆”。他回鄉(xiāng)后還草擬了一份《共產(chǎn)主義組建方案》。1871年5月15日,他寫了著名的理論著作《通靈者的信》(即《致杜牟尼的信》)提出了詩人自己關(guān)于詩歌問題的主張。幾乎與此同時,蘭波寫了十四行詩《母音》*(1871)(后來以“彩色十四行詩”而聞名),為象征派詩歌奠定了一塊堅(jiān)實(shí)的基石。1871年9月,蘭波應(yīng)魏爾蘭*之約,帶著自己的詩稿》醉舟》*等來到巴黎。不久即和魏爾蘭發(fā)生同性戀而同居。1873年7月在布魯塞爾,魏爾蘭竟開槍打傷蘭波。魏爾蘭入獄后,蘭波回到故鄉(xiāng),直至1875年,蘭波或在家鄉(xiāng),或赴英國、德國、意大利、瑞士旅游,他學(xué)會了七種外國語。1875年,蘭波寫完最后一部作品散文詩集《天啟集》,從此告別詩壇,斷然投入“冒險(xiǎn)家”的行列。1876年5月,他參加荷蘭殖民軍,到過雅加達(dá),三周后開小差。1877年又在漢堡一家馬戲團(tuán)中當(dāng)翻譯,并隨團(tuán)去過瑞典和丹麥。1880年去塞浦路斯,曾為該島總督監(jiān)造宮殿。后來又到過亞丁,在一家皮貨兼營咖啡的公司任職。1882-1883年,受該公司派遣,曾到非洲一些無人地帶進(jìn)行勘察。1887年,組織一支商隊(duì),向阿比西尼亞倒賣槍枝。1891年,右膝生腫瘤,五月回國在馬賽截去右腿,但仍無效,于這一年的11月10日病逝。死時年僅37歲。
蘭波的詩歌理論,集中反映在他的《通靈者的信》中。在這一有名的書信里,他提出要創(chuàng)造一種“不管從什么角度來理解都行”的詩歌語言;認(rèn)為詩人的首要任務(wù)是認(rèn)識自我,認(rèn)“我是一個他人”,“觀察它,體驗(yàn)它,研究它”,使“我”由一個“經(jīng)過推理的錯亂而成為一個通靈者”。他關(guān)于詩歌語言和“通靈者”的理論,為他的詩歌帶來了“明確與含糊相結(jié)合”的詩風(fēng),詩人描繪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也令人難以捉摸。他的十四行詩《母音》*就是他的藝術(shù)主張的實(shí)踐。在這一首詩中,他讓元音字母都代表一種顏色。字母、聲音、色彩渾然一體,而且互相轉(zhuǎn)換,形成視覺和聽覺的錯亂轉(zhuǎn)移,頗似波德萊爾*的《交感》。因此,《母音》被象征派的后起之秀奉為“通感”理論的第一個典范、啟示錄,奉為象征主義詩歌的奠基作。
蘭波的代表作除《母音》外,還有《醉舟》*(1871),后者被視為象征主義文學(xué)的代表作。另外尚有《在地獄中的一季》*(1873),散文詩集《天啟集》(1875)等。蘭波的詩現(xiàn)存140余首,大部分是他在非洲探險(xiǎn)時由別人經(jīng)手發(fā)表的。
蘭波的詩充滿了不滿現(xiàn)實(shí)的反抗激情,有些作品還是革命的熱情頌歌,這些都是可貴的。在形式上,他繼承并發(fā)展了波德萊爾的“通感”理論,為豐富詩歌的表現(xiàn)手段做出了貢獻(xiàn)。然而他的詩作形象光怪陸離,模糊紛繁,“通靈者”的內(nèi)心世界又是一片雜亂與神秘,不易于被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