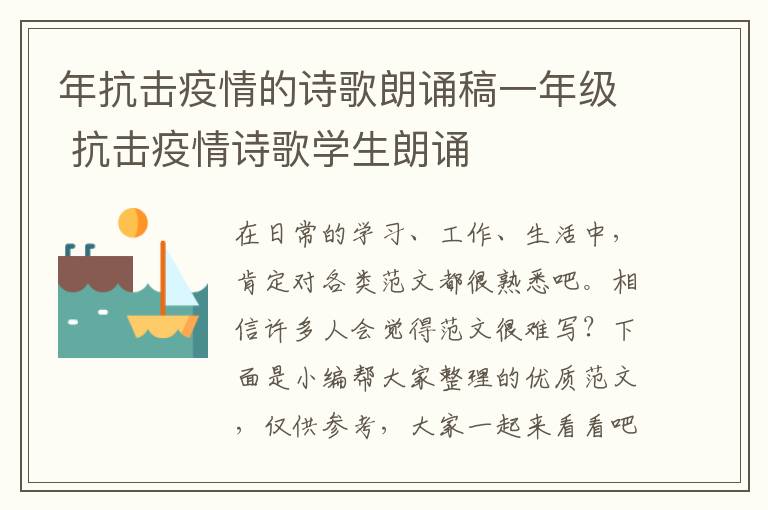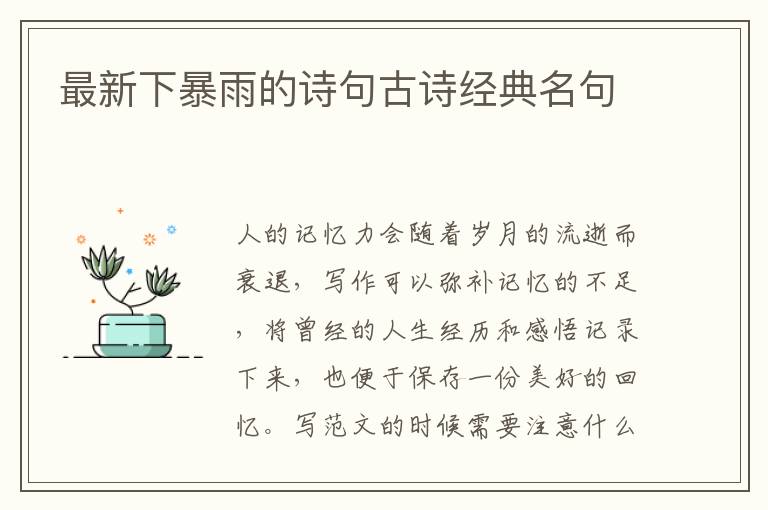《笛手》鑒賞

作者: 吳元成
龍仔
我是吹響四季的笛手,腳在泥土之上,在城市、鄉(xiāng)村和它們之間,我的笛音和我的微笑一樣傾灑在知覺到的事物上,這種美妙的手段得心應(yīng)手并深有來頭兒。我混跡人群,同時(shí)遠(yuǎn)遠(yuǎn)躲著他們。我的贊歌聽起來就象詛咒,深入情緒深處,制造一點(diǎn)傷痛。我不能說“不!”,因?yàn)樗竺媸呛诎档纳顪Y,是我的聽眾預(yù)知災(zāi)難的音符。我的笛音就這樣響起來。人群在道路上就這樣動起來。在我的笛音里,飛鳥的翅膀更純潔、更自由,藍(lán)色的天空離花朵好近,離愛情更近,愛情離真誠更近,就象我的笛音來自我手掌緊挨著的內(nèi)心。
真正的“笛手”
笛手,持笛之手,在空間和時(shí)間的邃道中強(qiáng)揚(yáng)著它美妙的旋律和深入人心的個(gè)性。
作者說:“我是吹響四季的笛手”。吹笛的人是笛手,作家和詩人也是笛手。當(dāng)年詩壇巨擘艾青從巴黎留學(xué)歸來,有人稱之為從歐羅巴歸來的“笛手”。艾青吹奏著,年輕的詩人也歌唱著。龍仔創(chuàng)作十余年,卓然一家,既風(fēng)流瀟灑,又深沉精微。
面對自然,面對生活,面對無所不在的“美”,笛手用手指觸摸,用口唇喚呼那“美”的、“真”的歌聲。這聲音來自自然,又歸于自然。“我的笛音”覆蓋“城市”、“鄉(xiāng)村”和一切“知覺到的事物上”。詩人并不是簡單地說“是”或“不”。因?yàn)樗靼住拔业馁澑杪犉饋砭拖裨{咒”。他并不是簡單地“歌頌”或者“詛咒”。對事物獨(dú)特的把握,對音樂獨(dú)特的展現(xiàn),個(gè)性也就孕育在其中。
“笛手”就是“敵手”,或者說不一定是“敵手”。笛手以一切不音樂的東西為敵,他把一切不音樂的東西排斥到音樂之外,他只吹奏合乎“律”的那種東西——這就是音樂,就是笛手存在的意義。同時(shí),他也不一定就是“敵手”—一最渾厚、最智慧、最美的自然似乎又是難以靠模仿能夠體味、能夠獲得的。這個(gè)時(shí)候的“笛手”仍然是也僅僅是“笛手”而已。
我欣賞這樣的語言:“我的笛音就這樣響起來。人群在道路上就這樣動起來。”笛音如歌如舞,如泣如訴,源于內(nèi)心,又抵達(dá)內(nèi)心,并引起心靈的震蕩。笛音響起來之后,也許一切仍歸于平靜,飛鳥還是飛鳥,藍(lán)天還是藍(lán)天,愛情還是愛情;也許就“動起來”,“人群”“動起來”,“飛鳥的翅膀更純潔、更自由,藍(lán)色的天空離花朵好近,離愛情更近”。為什么?
作者說:“笛音來自我手掌緊挨著的內(nèi)心。”
因此說這種笛手才是真正的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