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發(fā):溝通與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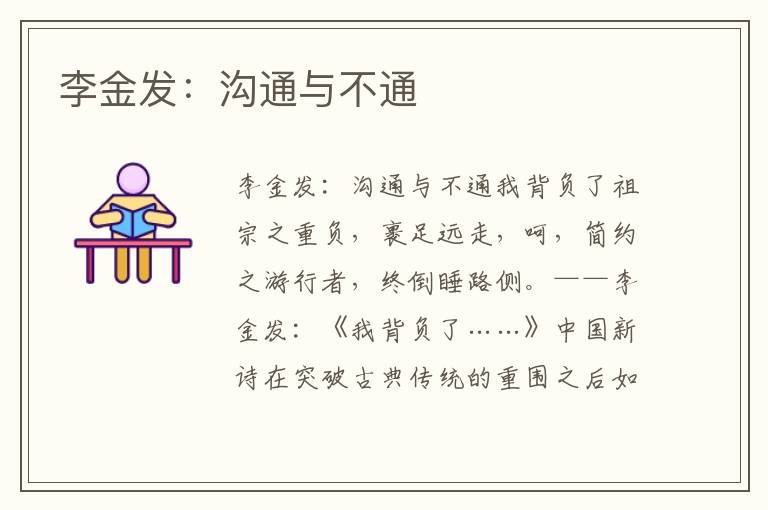
李金發(fā):溝通與不通
我背負了祖宗之重負,裹足遠走,
呵,簡約之游行者,終倒睡路側(cè)。
——李金發(fā):《我背負了……》
中國新詩在突破古典傳統(tǒng)的重圍之后如何尋求新的藝術(shù)資源,這是呈現(xiàn)在每一位詩人面前的難題,而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會注目于中外詩歌藝術(shù)的交融與溝通,雖然它最后可能還是一種美麗的空虛。
有意思的是,曾被以“詩怪”之名推離中國藝術(shù)傳統(tǒng)的李金發(fā)也有過溝通古典傳統(tǒng)的清晰表白:
余每怪異何以數(shù)年來中國古代詩人之作品,既無一人過問,一意向外采輯,一唱百和,以為文學(xué)革命后,他們是荒唐極了的,但從無人著實批評過,其實東西作家隨處有一思想、氣質(zhì)、眼光和取材,稍為留意便不敢否認,余于他們的根本處,都不敢有所輕重,惟每欲兩家所有,試為溝通,或即調(diào)和之意。
那么,在首先以西方象征主義詩風拉開與中國傳統(tǒng)距離的李金發(fā)這里,中外文化的溝通究竟有怎樣的特殊效果呢,或者說,李金發(fā)式的“溝通”最終是“通”還是“不通”呢?
這本身就是中國現(xiàn)代詩歌上的有趣話題。
1.象征主義:波德萊爾與馬拉美?
作為中國新詩象征主義的始作俑者之一,李金發(fā)首先是以他與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關(guān)聯(lián)而引人注目的,用李金發(fā)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受波德萊爾與魏爾倫的影響而作詩”,在李金發(fā)出現(xiàn)在中國詩壇的當時,人們發(fā)現(xiàn)的確還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長期于黑暗中號陶,在荒冢邊躑躅,在腐尸上呻吟;像他那樣大談死亡、疲憊,大談“世紀末”無法根除的憂患,像孫作云所指出的那樣:“在意識上,李先生的詩多描寫人生最黑暗的一面,最無望的部分,詩人的悲觀氣氛比誰都來得顯明。”因此,1920年代的中國詩歌很少有像李金發(fā)那樣接近波德萊爾、魏爾倫的氛圍與格調(diào)。
然而,若我們據(jù)此便說李金發(fā)是中國的波德萊爾、魏爾倫,或者說李金發(fā)詩歌就是波氏、魏氏之現(xiàn)代藝術(shù)在中國的體現(xiàn),卻未免失之輕率,至少沒有理解潛伏在這些現(xiàn)代痛苦之下的“另一個李金發(fā)”。
除了接近波德萊爾、魏爾倫的氛圍與格調(diào)之外,李金發(fā)的靈魂其實一開始就還存在“自己”的東西,我們不妨先讀一讀詩人的《題自寫像》:
即月眠江底,
還能與紫色之林微笑。
耶穌教徒之靈,
吁,太多情了。
感謝這手與足,
雖然尚少
但既覺夠了。
昔日武士被著甲,
力能搏虎!
我么?害點羞。
熱如皎日,
灰白如新月在云里。
我有草履,僅能走世界之一角,
生羽么,太多事了呵!
仍然是詩人慣用的估屈聱牙的詩句,不過我們仔細觀察,其主體精神卻似乎并不是現(xiàn)代主義式的:詩人欲自比拯救世人靈魂的耶穌教徒,卻立即自覺“太多情”了;想象做力拔山兮的打虎英雄,而又自慚形穢地“害點羞”。“我有草履,僅能走世界之一角”,人生苦短,七尺之軀,一掊黃土而已。這里似乎透出一股稀薄的“現(xiàn)代體驗”,不過統(tǒng)觀全詩,詩人最終還是相當自足的:“感謝這手與足,/雖然尚少/但既覺夠了。”微笑中的自信自持,頗具浪漫派風采,而言辭中的隨遇而安,自得自足,“獨善其身”,分明又是典型的民族傳統(tǒng)心理,尤其是這最后一句:“生羽么,太多事了呵!”
為了對照,我們不妨再讀一讀波德萊爾的《題自寫像》,其根本的差異便一目了然了:
我是傷口,同時是匕首!
我是巴掌,同時是面頰!
我是四肢,同時是刑車!
我是死囚,又是劊子手!
我是吸我心的吸血鬼,
——一個被處以永遠的笑刑。
卻連微笑都不能的人
——一個被棄的重大的犯罪者!
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要做的不是炫耀自我的自信自足,恰恰相反,他要攪碎這個自足自圓的狀態(tài)。“我是傷口”,但卻無意尋找一個療治的避難所,相反,他還要與匕首為伍!“我是巴掌”,但它并不迎擊作惡的敵人,因為“我”本身就是惡,我打的也是自己……為了自我的解放和發(fā)展,人類創(chuàng)造了文明,而文明一旦建立,卻成了人自身的枷鎖與牢籠。這個愈見清晰也愈見殘酷的現(xiàn)實教育了自波德萊爾以降的現(xiàn)代西方人,他們對人的自身的永恒性、穩(wěn)定性的傳統(tǒng)信仰破滅了,籠罩在心中的是叔本華式的兩難陰霾,無所適從的悲劇性體驗,因而對他們而言,任何自滿自信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幻夢而已。
就這樣,波德萊爾的“我”就成了反諷的自嘲自虐的“我”,而李金發(fā)的“我”卻是自足自信的、完完整整的“我”。痛苦歸痛苦,號陶歸號陶,李金發(fā)心靈深處的那塊理想的、光明的空地卻是守護得好好的,與現(xiàn)實的腐朽無干。在“世紀末”的主題中,詩人李金發(fā)的眼前還不時晃動著新世紀美麗的光環(huán)。世界雖如“蜂鳴”般喧囂、煩惱,讓人坐立不安,但是,我們?nèi)钥赡堋靶煨性谔祀H”、沐浴于陽光(《給蜂鳴》)。這與波德萊爾滿眼的丑惡破碎當然不一樣。似乎,李金發(fā)所擁有的文化傳統(tǒng)也不允許他把世界人生一眼“穿”。這樣的詩句是李金發(fā)不會有的:“虛無也將我們欺騙?/一切,甚至死神也在/對我們說謊?”(波德萊爾《骸骨農(nóng)民》)
面對這個丑惡的病入膏肓的世界,波德萊爾的理想只能在遙遠的依稀的彼岸,只能在迷離的幻覺中:“當我再睜開火眼觀照,/看到我恐怖的陋室,/大夢初醒,我心中感到/被詛咒的憂傷和尖刺。”海市蜃樓,去來匆匆!而李金發(fā)的理想?yún)s要現(xiàn)實、扎實得多。“遠游西西利之火山與地上之沙漠”(《給蜂鳴》),這個要求并不過分。那個下午的暖氣也是呼之欲出的:“擊破沉寂的惟有枝頭的春鶯,/啼不上兩聲,隔樹的同僚/亦一起歌唱了,贊嘆這嫵媚的風光。”(《下午》)欣然投入某個現(xiàn)實角落的懷抱,這倒是浪漫主義詩人的情愫了。
如果說,無家可歸是現(xiàn)代主義者的共同苦惱,那么李金發(fā)倒不是沒有“家”,而只是一位迷路者,有著“游獵者失路的叫喊”。因而,作為一位尋覓者,一位暫時受挫的孤膽英雄,他也有必要保護自足自信的心態(tài),而不大可能產(chǎn)生那種自我分裂的感覺。
詩人還相信:“呵,我所愛!上帝永遠知道,/但惡魔迷惑一切。”(《丑行》)看來,在李金發(fā)這里,并非“上帝死了”,只不過是摩菲斯陀在游獵者的歸途樹立了一面面“鬼打墻”。世界的破碎,是魔鬼的肆行,“一切成形與艷麗,不是上帝之手創(chuàng)了”(《丑》):世界原來也是和諧的,“我的孩童時代,為鳥聲喚了去,/呵,生活在那清流之鄉(xiāng),居民依行杖而歌,/我閉目看其沿溪之矮樹”(《朕之秋》)。苦難只是不測之禍,我們也還有機會向上帝哀告、哭訴(《慟哭》),希望雖如“朝霧”,但畢竟還是希望(《希望與憐憫》)。
這樣,李金發(fā)也始終相信,這個世界盡管丑惡太多,但美并非只是理想,他時常呼喚現(xiàn)實的美以驅(qū)散丑。“吁!這緊迫的秋,/催促我們amour之盛筵!/去,如你不忘卻義務(wù),我們終古是朋友。”(《美神》)
到此,我們似可以解開這個疑團:作為象征主義的李金發(fā),一方面受波德萊爾、魏爾倫的影響,另一方面卻又認為自己與繆塞等浪漫主義詩人“性格合適些”。因為,繆塞就是一個不斷尋找理想又不斷失望的(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天涯飄零”者形象。他有一顆孤傲的心,時常感到個體的“我”與群體的他人的隔膜。孤獨是浪漫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的共同體驗,但浪漫主義的繆塞多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清高,這與李金發(fā)“我覺得孤寂的只是我”(《幻想》)是契合的。
繆塞雖不斷失望,卻也時常勉勵自己:“我已決定遠走高飛,/走遍天涯的南北東西,/去尋找殘存的一線希望。”不斷地走,雖是行路難,但信念猶存。“據(jù)說,人從本性上看,主要是善良的,只是受到了這個世界中邪惡力量的侵蝕。有一種與此類似的信仰認為:對理想的追求可能使個人和社會都得到完善。事實上,浪漫主義的各個方面都包含著這樣那樣的理想因素。”③李金發(fā)與繆塞一樣,都表現(xiàn)出了這樣的信仰與理想,他們都屬于這理想籠罩下的“飄泊者”與“游獵者”。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反封建、爭個性的時代主題始終或顯或隱地貫穿著,浪漫主義的理想光輝深孚人心。盡管作為一種完整運動的浪漫主義可能是短暫的,但是,其精神卻依然對眾多的作家產(chǎn)生了潛在的影響。正如不少研究者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實踐者們許多都是站在浪漫主義的立場上取舍“現(xiàn)代體驗”的。
2.作為人格氣質(zhì)的傳統(tǒng)
任何一種文學(xué)思潮的輸入,都必須經(jīng)受時代特征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雙重篩選。李金發(fā)醉心于西方象征主義,但時代大主題卻使他拋不開浪漫的理想,更難改變的是民族的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
“哭”與哀愁、呻吟是李金發(fā)慣有的抒情方式,“黑夜長久之痛哭”(《十七夜》),“衰老的裙裾發(fā)出哀吟”(《棄婦》),“遠處的風喚起橡林之呻吟”(《遲我行道》),這些突破了傳統(tǒng)和諧美的意象是李金發(fā)詩歌之于中國現(xiàn)代詩壇的一大貢獻。但是,從更深的層面講,它又依然存在著特有的民族心理積淀。比如從心理學(xué)上講,能哭并非大悲,至少它還有痛苦的具體原因,包括還有這個較好的消解方式。真正大悲而絕望者,是不能明確痛苦的具體原因,也找不到發(fā)泄解脫的具體手段的,如墮冥冥之中而四面受敵,欲呼不能,四喊不應(yīng),困頓之極,已無所謂眼淚。我們應(yīng)該看到,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尤其是后期象征主義詩歌中很少見到“哭”、“眼淚”這類哀哀怨怨的傾訴,那里多是一種靈魂被風干曝曬得吱吱有聲的感覺,如波德萊爾“茫茫深淵上面,/搖我入睡。時而,又風平浪靜,變成/我絕望的大鏡”(波德萊爾《音樂》)。
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提供給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實現(xiàn)之路是狹窄的,專制體制造就的依附性生存在中國知識分子那里形成了一種被歷史學(xué)者稱之為“臣妾人格”的心理狀態(tài),委曲求全、內(nèi)向柔弱的精神趨向應(yīng)運、而生。哭、哀愁、呻吟便是這種心理的自然流露。同樣的憂傷痛苦,在李金發(fā)與法國象征主義詩人那里是很有差異的。
比如,同是借酒澆愁,李金發(fā)是“我酒入愁腸,/旋復(fù)化為眼淚”(《黃昏》),痛苦之情需要在眼淚中流出,心境盼望重新穩(wěn)定。而波德萊爾則是:“就在同樣的譫妄之中……/逃往我夢想的樂園。”(《情侶的酒》)酒醉并不能夠取消夢想的超越意識。
再如,李金發(fā)和魏爾倫都喜歡以琴抒懷。李金發(fā)的琴聲象征著自我的理想,“奏到最高音的時候,/似乎預(yù)示人生的美滿”。只是,有外來的強力要沖擊它:“不相干的風,/踱過窗兒作響,/把我的琴聲,他震得不成音了,”而真正的悲劇卻在于:“她們并不能了解呵。”在這里,悲劇被定義在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當中,也是人倫關(guān)系的隔膜造成了自我精神的不適,人倫關(guān)系的擠壓導(dǎo)致了詩人呻吟似幽怨:“我若走到原野上時,/琴聲定是中止,或柔弱地繼續(xù)著。”(《琴的哀》)。而魏爾倫的琴聲,與其說是一種明確的理想,毋寧說是一種無端的嘆息,一種莫名的情緒:“一股無名的悲緒,浸透到我的心底。”(《秋歌》)更重要的是,魏爾倫明確宣布,自己的悲哀與人際關(guān)系無關(guān):
淚水流得不合情理,
這顆心啊厭煩自己。
怎么?并沒有人負心?
這悲哀說不出情理。
超越了個人的社會關(guān)系的壓力,魏爾倫的痛苦來自他對生命與世界的更深的思考與關(guān)懷:“這是最沉重的痛苦,/當你不知它的緣故。/既沒有愛,也沒有恨,/我心中有這么多的痛苦!”
應(yīng)當看到,李金發(fā)詩歌的許多哀怨都與個人的愛情體驗有關(guān)。李金發(fā)的許多愛情詩都給人這樣一個感覺,仿佛詩人在吃力地追逐著理想的對象,卻多半是可望而不可即,我們的詩人疲于奔命,終于累倒在人生的中途:“我背負了祖宗之重負,裹足遠走,/呵,簡約之游行者,終倒睡路側(cè)。”(《我背負了……》)疲憊感與柔弱感是一脈相承的。
于是,這樣的詩人需要“手杖”:“呵,我之保護者,/神奇之朋友,/我們忘年地交了。”(《手杖》)
于是,這樣的愛情充滿了“戀母情結(jié)”:“你壓住我的手,像睡褥般溫柔,我的一切/管領(lǐng)與附屬,全在你呼吸里”(《無題》);“我在遠處望見你,沿途徘徊/如喪家之牲口”(《印象》);“我恨你如同/軛下的弩馬,/無力把韁條撕破,/如同孩子怨母親的苛刻……一”(《我對你的態(tài)度》)此時的李金發(fā)正生活在巴黎。
巴黎,作為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縮影,用巴爾扎克名著《高老頭》中的概括來說,就是“一方面是最高雅的社會的新鮮可愛的面目,個個年輕,活潑,有詩意,有熱情,四周又是美妙的藝術(shù)品和闊綽的排場;另一方面是濺滿污泥的陰慘的畫面,人物的臉上只有被情欲掃蕩過的遺跡”。
一個青年,一個來自古老東方、具有擺脫不掉的傳統(tǒng)心理的青年,面臨一種反差巨大的生活:沖動與壓抑,熱烈與自卑,人性與獸性,現(xiàn)實渴望與心理重負……所有這些外在的吸引與內(nèi)在的自我抗拒都令一個柔弱、疲憊的靈魂苦不堪言。這與郁達夫留日經(jīng)歷大約有些相似,不過郁達夫更多些“暴露癖”,甘愿無情地解剖自己,而李金發(fā)似乎更愿意自我掩飾一些。
我認為,李金發(fā)詩歌的佶屈聱牙可以從這里得到部分的解釋:它來源于詩人對人生欲望的羞澀心理,欲言又懼,如履薄冰,戰(zhàn)戰(zhàn)兢兢,遮遮掩掩,詩人仿佛總在回避著某些切膚之痛。
不錯,李金發(fā)是中國詩壇上少有的公開書寫“死亡”、“黑暗”、“恐懼”等深層心理的人,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所有這些抒情大多只出現(xiàn)在一些抽象的概括性的描繪中,一當進入具體的人生細節(jié),特別是觸及詩人的親身體驗之時,他的文字變就閃閃爍爍起來了。如《給Jeanne》,面對這位法國少女,詩人有些什么意念呢,是“同情的空泛,/與真實之不能期望么?無造物的權(quán)威,/禁不住如夜螢一閃”。“同情的空泛”大約是現(xiàn)實,“真實”大約指“真實的感情”,接下去,應(yīng)當是“我”無造物的權(quán)威,所以不能左右你,“夜螢”估計是暗示少女閃爍的眼睛吧。這是一種愛而不得所愛,但又不能克制內(nèi)心欲念的復(fù)雜心理。內(nèi)向的羞澀的詩人在這個時候是不會直抒胸臆的,他有意無意地采用了象征主義的暗示、省略手法。如果這種手法在詩中多一些,詩就會顯得別別扭扭、晦澀難懂了。
傳統(tǒng)在李金發(fā)這里主要不是指一種藝術(shù)的境界,而是他無法改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一種與生俱來的人格氣質(zhì)。因為,雖然詩人表示他試圖在中國古典與西方之間有所溝通和調(diào)和,然而,我們在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讀到的卻不是更圓熟的古代藝術(shù)技巧與品質(zhì),而是一種源遠流長的處世心態(tài)與人格模式。
中外藝術(shù)的溝通,對李金發(fā)而言還只不過是一種初步的想法。
3.晦澀與不通
以上我們試圖用中國知識分子九曲回腸式的傳統(tǒng)心理習(xí)慣來解釋李金發(fā)詩歌的語言晦澀問題,但這也只能適用于部分詩歌。羞澀扭曲的含蓄在現(xiàn)代只是中國人的一種深層心理,詩人不可能時刻都處于羞澀、遮掩之中,我們還需要將詩人的精神氣質(zhì)與他的知識結(jié)構(gòu)、詩歌修養(yǎng)結(jié)合起來作一些新的綜合性分析。
一個藝術(shù)家的文化心理與他理性層次的知識結(jié)構(gòu)密切相關(guān),最終影響了藝術(shù)的取舍。就知識結(jié)構(gòu)而言,他同時接受了西方浪漫主義詩歌與象征主義詩歌,就深層文化心理來說,他又具有明顯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人格氣質(zhì)。這樣幾個方面的藝術(shù)指向并非一致。比如浪漫主義的樂觀理想就不斷銷蝕著“世紀末”幽邃的思索,引導(dǎo)詩人在自足自信中堅定地面向現(xiàn)實,詩人表面濃郁厚重的現(xiàn)代主義意識實際就被抽空著、瓦解著,同時,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人倫關(guān)懷則根本上改造了西方象征主義生命關(guān)懷的宏大主題,引導(dǎo)詩人在細碎的人間憂傷中傾訴個人難以啟齒的故事與感受。
但問題在于,法國象征主義詩歌所承載的現(xiàn)代體驗與現(xiàn)代表達已經(jīng)對中國留學(xué)生構(gòu)成印象深刻的一種“知識”,一種似乎是當代人“應(yīng)該”掌握并接受、應(yīng)用的知識,李金發(fā)本人無法拒絕這樣的時代誘惑。這是一種相當難以解決的自我的矛盾:心靈深處的氣質(zhì)與理性層次的知識追求這樣不和諧。于是,我們會發(fā)現(xiàn),李金發(fā)的創(chuàng)作不斷呈現(xiàn)出幾種力量的消長。當他哭訴理想的渺茫、追求的阻礙,或構(gòu)筑自己的伊甸樂園之時,詩歌朦朧而韻味十足,但認真分析,此時此刻的李金發(fā)詩歌多半與文學(xué)史上所贊揚的那個象征主義詩人無關(guān);當他刻意以象征主義為旗幟,在詩歌中堆砌現(xiàn)代意象與色彩之時,又往往脫離開了自己精神深處的支撐,所以時常顯得意念化、抽象化。如果再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詩歌的內(nèi)在情緒是不連貫的,許多“現(xiàn)代”味是黏上去的。
比如,當對“時間”的現(xiàn)代性煩憂成為一種先驗的意念時,就會在許多并不一定涉及時間問題的情態(tài)中莫名其妙地鉆出來。在那首公認的代表作《棄婦》中,有“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訛成灰燼……”全詩的情緒還是基本連貫的,但“時間”這個詞,冒得太唐突,太抽象,太扎眼了。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不可勝數(shù)的“時間”憂患詩中,所有的“時間”都是具體、可感、切實的,是一個內(nèi)涵豐富的立體物。李金發(fā)還有一首《時間的誘惑》,這本身也是一個內(nèi)腹開闊,可以充分挖掘的題目,然而讀完全詩才知道,詩人對時間到底有哪些“誘惑”,又如何“誘惑”,其實知之不多,每每蜻蜓點水,點得再多,水也沒有上來多少。
知識與概念一旦脫離開人的真實感受,就可能出現(xiàn)那種超感覺的人為拔拽,它最終將破壞全詩的情緒氣氛,造成詩情血液中的許多癌塊,這種例子在李金發(fā)那里是不少的。比如稱風和雨是世界的“何以”,春夏秋冬是世界的“然后”這種理念化的比喻(《我認識風與雨》);如“我愛無拍之唱域詩句之背誦”(《殘道》)這樣毫無必要的別扭的句式。有時詩人還有意追求一種哲學(xué)味,如“語言隨處流露溫愛/但這‘今日’‘明日’使我兒/病病倒了”(《北方》)。然而,西方現(xiàn)代詩歌的哲學(xué)感并不是用哲學(xué)的概念連綴起來的,它是融入詩人的血液之中,從詩人最平實最真切的體驗中“蒸餾”出來的。
不管是哲學(xué)意識還是現(xiàn)代精神,優(yōu)秀的詩歌總是以一個“整體”來實現(xiàn)的,如果其意義只能靠幾個現(xiàn)代味的專有名詞來實現(xiàn)(甚至還打上引號讓人注意),那將是一件可悲的事。大家都愛引李金發(fā)的名句:“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不錯,句子是精彩而極有現(xiàn)代主義感受的,但可惜在那首《有感》中也只有這么一個孤零零的句子,而且很難想象它是怎么鉆進去的。這倒好像是中國古人的一種作詩方式,偶有佳句,再前后補綴,“詩眼”很醒目;只是若“有感”的只有這么一句,那還是不要勉強補綴的好。
此外,詩人本身的詩歌修養(yǎng)(特別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語言修養(yǎng))也從根本上決定著詩歌表達的成功。馬拉美曾說過:“晦澀或者是由于讀者方面的力所不及,或者由于詩人的力所不及。”在這里,中國讀者的“現(xiàn)代”感受我們是無法確切定位的,可以分析的倒是李金發(fā)自身的詩歌創(chuàng)作能力——詩歌修養(yǎng)。
作為客家人的李金發(fā),其使用的母語在詞匯、句法等方面都與詩歌寫作的書面漢語有相當?shù)木嚯x,詩人必須克服這樣的距離才能將自己的本能思維形式與通用的表達形式結(jié)合起來。問題是他做到了嗎?與詩人頗多接觸的人們都不斷給我們傳達著這樣的信息:李金發(fā)“是廣東人,是華僑,在南洋群島生活,中國話不大會說,不大會表達”。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它基本上注定了詩人創(chuàng)作的某種失敗。
不僅如此,孫席珍先生還透露說:詩人“法文不太行”,“又言書也讀了一點,雜七雜八,語言的純潔性沒有了”。“引進象征派,他有功,敗壞語言,他是罪魁禍首。”敗壞語言,這對于一個視語言為生命的詩人來說,無疑是最嚴重的指責,如果對于其嚴重性我們還可能有所懷疑的話,同樣作為象征主義追求者的卞之琳的旁證就值得我們冷靜思考了。卞之琳斷定,李金發(fā)“對本國語言幾乎沒有一點感覺力,對于白話如此,對于文言也如此,而對于法文連一些基本語法都不懂”。
在這個時候,李金發(fā)對他設(shè)想的中外詩歌溝通顯然就力不從心了。甚至,不僅無法完成更高的溝通,就是實現(xiàn)自身創(chuàng)作的順通,都相當?shù)仄D難。
在現(xiàn)代詩歌藝術(shù)中,晦澀是一種新的美學(xué)效果,但美學(xué)意義的晦澀是思想繁復(fù)、感覺深密的一種形式,與表達上的不順暢根本不是一回事。正如瓦萊里所說,在現(xiàn)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應(yīng)該“旋律毫不間斷地貫穿始終,語意關(guān)系始終符合于和聲關(guān)系,思想的相互過渡好像比任何思想都更為重要”。李金發(fā)詩歌的文白夾雜在某種意義上是他急于尋找語言資源的一種焦躁,而尋找并沒有更深的語言修養(yǎng)為基礎(chǔ)之時,就很可能墮入不通的尷尬了。
從竭力溝通到相當不通,詩人李金發(fā)留給我們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都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