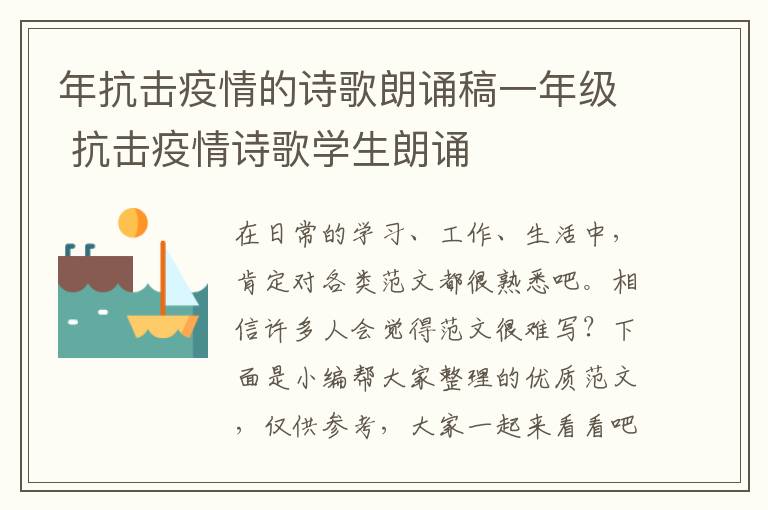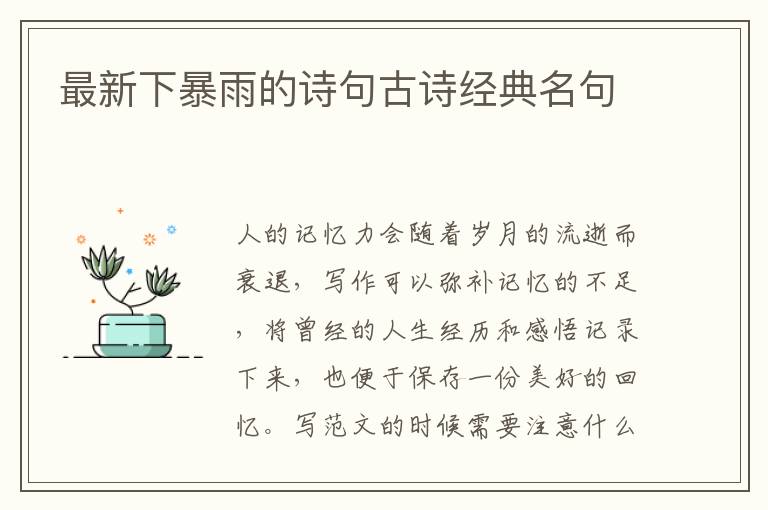斯洛伐克詩歌

斯洛伐克詩歌
直到上世紀(jì)末,斯洛伐克人實(shí)際上根本沒有本族語的文學(xué);拉丁語和捷克語一直被作為書面語言使用,用斯洛伐克語寫作僅僅是一些零星的嘗試。17世紀(jì)出現(xiàn)的兩部偉大的贊美詩集:新教的《至圣的詩琴》(1636)和天主教的《天主教格萊哥列圣歌旋律》(1655),也許可以被看作是民族文學(xué)的開端。第一部詩集所匯集的大部分是捷克語贊美詩,但也有一些是用斯洛伐克語寫成的,并且使用了本族方言的表達(dá)方式。《天主教格萊哥列圣歌旋律》中的語言,代表了特爾那瓦大學(xué)的耶穌學(xué)會成員,使用斯洛伐克西部方言進(jìn)行寫作的嘗試。在整個(gè)17世紀(jì)的后半葉和18世紀(jì)的大部分時(shí)間,即斯洛伐克的巴羅克時(shí)期,詩歌一直幾乎完全是宗教性或說教性的。
18世紀(jì)末和19世紀(jì)的前30年,新古典主義在斯洛伐克文學(xué)中占主導(dǎo)地位。在這一期間,一位叫安樂·貝諾勒克(1762—1813)的天主教教士為使斯洛伐克語規(guī)范化,做了一次新的嘗試。貝諾勒克使用的斯洛伐克語也同樣是以斯洛伐克西部方言為基礎(chǔ)的。他的追隨者揚(yáng)·霍利(1785—1849),從古代詩人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的靈感,寫出了很多冗長的、以愛國主義歷史為主題的史詩。貝諾勒克使用的斯洛伐克語未能被公眾接受,注定了霍利的作品必將湮沒的命運(yùn)。用捷克語寫作的揚(yáng)·科拉爾(1793—1852)要成功得多。他在杰出的十四行組詩《斯萊瓦的女兒》(1824年)中,為斯洛伐克民族的軟弱無能而痛惜,但卻預(yù)見他們將成為一個(gè)偉大的民族。
直到19世紀(jì)40年代,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出現(xiàn)時(shí),規(guī)范的、有生命力的斯洛伐克語才開始形成。它以斯洛伐克中部方言為基礎(chǔ),因此得到更加廣泛的接受;這一規(guī)范語的產(chǎn)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兩位新教民族主義者:盧德維特·什圖爾(1815—1856)和J·M·胡爾班(1817—1888)努力的結(jié)果。圍繞在什圖爾周圍的浪漫主義詩人,受到斯洛伐克民歌的強(qiáng)烈影響;作為強(qiáng)烈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將民族文學(xué)定義為使用通俗語言和民間形式的文學(xué)。他們最終解決了詩律問題(這個(gè)問題曾使斯洛伐克詩人感到幾乎同語言問題一樣傷腦筋):他們既使用了音長音節(jié)詩體,也使用了音強(qiáng)音節(jié)詩體。這時(shí)的浪漫主義詩人以民歌為典范,采納了以重音為節(jié)奏的音強(qiáng)音節(jié)詩體。
什圖爾的作品有《黃昏遐想》,這部詩集控訴了社會的不平等。這一代浪漫主義作者當(dāng)中,還包括許多重要詩人。安德烈·斯拉德科維奇(1820—1872,翁德烈·布拉克薩特利斯之筆名)創(chuàng)作了歷史詩《德特瓦人》(1853)。這部史詩對德特瓦地區(qū)農(nóng)民生活的描寫樸素而精確。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揚(yáng)科·克拉爾(1822—1876)創(chuàng)作了含有戀母情結(jié)主題,富于情趣的民謠。揚(yáng)·博托(1827—1881)創(chuàng)作的《亞諾西克之死》(1862年)歌頌了喀爾巴阡山中一位有名的土匪,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已成為自由的象征。揚(yáng)·卡林西亞克(1812—1871)的創(chuàng)作,使用有關(guān)民族歷史的主題,但比其他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有更多的寫實(shí)細(xì)節(jié)。
1848年革命的失敗,使這一代浪漫主義詩人對自由所寄托的希望破滅了。隨著19世紀(jì)的消逝和匈牙利統(tǒng)治的日趨嚴(yán)酷,一種絕望的情緒開始形成。斯韋托扎爾·胡爾班·瓦揚(yáng)斯基(1847—1916)和使用帕·赫維茲多斯拉夫這一筆名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帕沃爾·奧爾薩格(1849—1921),是這一時(shí)代最偉大的詩人。胡爾班·瓦揚(yáng)斯基是J·W·胡爾班的兒子,是一位浪漫主義詩人,但他的詩歌卻具有斯洛伐克文學(xué)中前所未有的諷刺和冷嘲風(fēng)格。赫維茲多斯拉夫是高蹈派詩人,曾翻譯過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以及其他詩人的作品,這些翻譯作品給斯洛伐克詩歌帶來了新的激勵(lì)。赫維茲多斯拉夫信奉世界主義,因此盡管當(dāng)時(shí)民謠形式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一直占主導(dǎo)地位,他卻避而不用。盡管他是一位創(chuàng)作過抒情詩、史詩和戲劇詩的詩人,但他的代表作卻可能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恐怖的《血腥的十四行詩集》(1919)。雖然他最終看到斯洛伐克贏得了自由,但他晚期的詩作卻越來越充滿幻滅感。
象征主義也被斯洛伐克人叫做“現(xiàn)代派”,它的代表詩人是伊萬·克臘斯科(生于1876,揚(yáng)·博托的兒子)。克臘斯科同赫維茲多斯拉夫一樣持有悲觀主義觀點(diǎn),但他的詩作在語言的使用以及象征主義內(nèi)省感覺的微妙用法上,要更現(xiàn)代一些。揚(yáng)克·耶森斯基(1874—1945)在自己的詩作中形成了斯洛伐克詩歌中鮮有的世界主義的諷刺風(fēng)格。在近期出現(xiàn)的詩人中,埃米爾·B·盧卡奇(生于1900)是一位受保爾·克勞戴爾影響,復(fù)雜而矛盾的宗教詩人。揚(yáng)·斯姆萊克(生于1899,揚(yáng)·齊埃特克的筆名)是一位活力論者,以對女性美的肉感描寫為樂。他也曾涉足詩化主義,一種產(chǎn)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詩歌運(yùn)動(dòng)。這次運(yùn)動(dòng)始于20世紀(jì)20年代,具有未來主義、達(dá)達(dá)主義和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特征(見各條)。另一位詩化主義詩人是拉克·諾沃麥斯基(生于1904),他是一位記者,和揚(yáng)·波尼昌(生于1902)等無產(chǎn)階級詩人以《人群》雜志為園地發(fā)表作品,為無產(chǎn)階級文學(xué)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影響斯洛伐克詩歌的主要外國文學(xué)有捷克、德國和俄國文學(xué)。同捷克語一樣,斯洛伐克語的重音一律落在第一音節(jié)上,這便利了揚(yáng)抑格節(jié)奏的使用。然而,行首音步的音律具有相當(dāng)自由的抑揚(yáng)格詩歌仍很常見,在19世紀(jì)的后半葉比揚(yáng)抑格詩歌更為流行。純?nèi)匾袈墒聦?shí)上是不可能存在于斯洛伐克語中的,因?yàn)橹匾敉湓诿恳黄鏀?shù)音節(jié)上。然而揚(yáng)抑抑格音步可以同揚(yáng)抑格音步交替使用;在浪漫主義時(shí)期以及當(dāng)代,這種純聲調(diào)節(jié)奏由于古代音律以及本地民謠的影響而非常流行。
斯洛伐克民族問題的嚴(yán)重性以及許多斯洛伐克作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給斯洛伐克詩歌披上了一種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凡是有助于表達(dá)或暗示愛國思想的詩歌形式都非常風(fēng)行:如敘事詩,即興詩、流行歌曲及沉思抒情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