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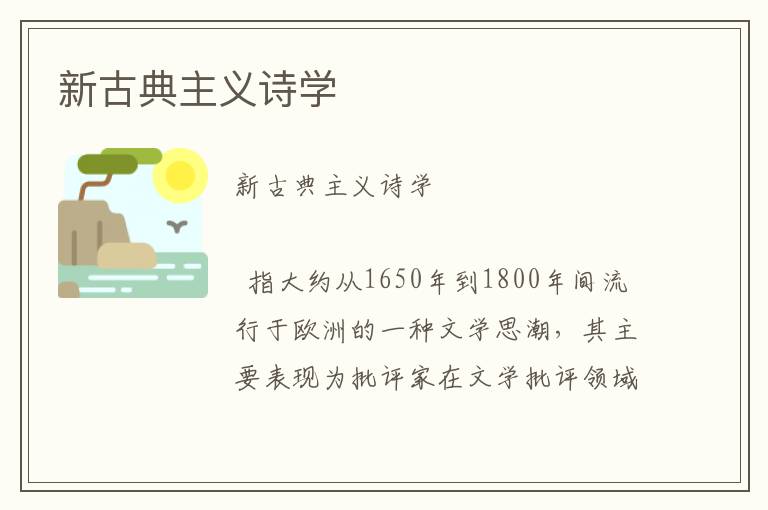
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
指大約從1650年到1800年間流行于歐洲的一種文學(xué)思潮,其主要表現(xiàn)為批評(píng)家在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中惟獨(dú)鐘情于詩(shī)學(xué),尤其是指批評(píng)界對(duì)詩(shī)人和詩(shī)歌的本質(zhì)及價(jià)值所做的探討。當(dāng)然這種探討并不是要建立一套詩(shī)學(xué)原則和信條的體系,其發(fā)展也不是單一的、有條不紊的。有時(shí),“藝術(shù)”是批評(píng)家討論的重點(diǎn)(如布瓦洛、拉潘、勒博敘、德萊頓、戈特舍德、萊辛等)。有時(shí)“自然”又成了討論的重點(diǎn)(如約翰遜、揚(yáng)、盧梭、赫爾德等)。還有的時(shí)候,詩(shī)的目的或效果又成了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如布瓦洛、拉潘、德萊頓、艾迪生、約翰遜等)。而對(duì)詩(shī)的目的的討論正是這一思潮的主要特征。當(dāng)然批評(píng)家還對(duì)詩(shī)人的才能和創(chuàng)作習(xí)慣進(jìn)行了討論(如布烏爾、約瑟夫·沃頓、揚(yáng)等)。不同時(shí)期的討論既有區(qū)別又有重疊,批評(píng)家使用的方法不盡一致,堅(jiān)持的詩(shī)歌原則也是因人而異。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不同討論的脈絡(luò)及特點(diǎn),也能夠勾勒出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發(fā)展中的變化、趨勢(shì)和重點(diǎn)。
一、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關(guān)于詩(shī)的本質(zhì)、問題和美點(diǎn)的討論
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在這方面呈現(xiàn)兩種主要的特征:有些討論側(cè)重于詩(shī)的“技巧”方面,有的側(cè)重于詩(shī)的“質(zhì)量”方面。二者在討論詩(shī)歌的問題和現(xiàn)象時(shí)具有明顯的差異。“技巧”詩(shī)學(xué)師承賀拉斯和亞里士多德。這派詩(shī)學(xué)家所探討的問題和使用的術(shù)語無不源于這兩位古人的詩(shī)學(xué)論述,但他們的解釋竭力彌合賀拉斯和亞里士多德在詩(shī)學(xué)見解上的嚴(yán)重分歧。此外,這派詩(shī)學(xué)家還繼承了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和17世紀(jì)批評(píng)家的傳統(tǒng),將賀拉斯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與西塞羅、昆提利安及一些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詩(shī)論融為一體。“技巧”詩(shī)學(xué)的代表作有德萊頓的《論戲劇詩(shī)》和他為莎士比亞劇作《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dá)》所寫的序言、菲爾丁為其《約瑟夫·安德魯斯》所寫的序言、布瓦洛的《詩(shī)藝》、拉潘的《關(guān)于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的思考》、伏爾泰為其《奧狄浦斯王》所寫的序言、盧桑的《詩(shī)論》、戈特舍德的《為德國(guó)人寫的批判詩(shī)學(xué)試論》、萊辛的《漢堡劇評(píng)》、格拉維納的《詩(shī)學(xué)原理》和《論悲劇》、梅塔斯塔西奧的《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精義》等。這派批評(píng)家主要試圖根據(jù)詩(shī)的目的和不同體裁的寫作方法,回答有關(guān)詩(shī)的藝術(shù)和結(jié)構(gòu)的問題。他們?cè)谡撌鲈?shī)的“藝術(shù)”、魅力、詩(shī)人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和讀者的需求中,推演出了許多法則和構(gòu)成美的因素。
而“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繼承了迪米特里厄斯,狄奧尼西奧斯、昆提利安、西塞羅,尤其是朗吉努斯的詩(shī)學(xué)傳統(tǒng),根據(jù)讀者的要求、詩(shī)人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和才能,提出了一套詩(shī)學(xué)原則。這派批評(píng)家試圖回答具體形式和技巧以外的問題。他們所探討的是有關(guān)詩(shī)作質(zhì)量或價(jià)值的問題。而正是這種質(zhì)量和價(jià)值形成了詩(shī)歌的總體特點(diǎn)以及不同詩(shī)人在風(fēng)格上的差別。這派批評(píng)家或則不顧體裁和風(fēng)格的差異,或則將體裁和風(fēng)格納入主題、思維、觀點(diǎn)、風(fēng)尚、表現(xiàn)方式等更大的問題之中加以討論;其代表作有德萊頓為《寓言集》所作的序言、蒲柏為《伊利亞特》所作的序言、約翰遜關(guān)于詩(shī)歌的許多隨筆、伏爾泰的《悲劇論》、博德默爾的《論詩(shī)之美》、J·E·施萊格爾的《莎士比亞與安德烈亞斯·格里菲斯比較》、卡萊皮奧的《法意悲劇詩(shī)比較》等。
在“技巧”詩(shī)學(xué)和“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的發(fā)展過程中,就一般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和美學(xué)原則而言,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還產(chǎn)生了另外兩種批評(píng)方法。它們?cè)诰唧w的文論中與“技巧”詩(shī)學(xué)和“質(zhì)量”詩(shī)學(xué)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其中之一是,歷史學(xué)家和批評(píng)家越來越關(guān)注特殊的修辭背景,環(huán)境的影響和作品的歷史背景。這種歷史背景包括詩(shī)人的才能、受教育程度、生活經(jīng)歷、讀者、地理環(huán)境、氣候、民族、語種以及詩(shī)人所處時(shí)代的精神。批評(píng)家通過對(duì)上述各方面的考察,可以對(duì)不同民族、不同時(shí)代和不同社會(huì)特殊的詩(shī)歌形式以及作品質(zhì)量做出評(píng)價(jià)。這方面的論著有:多比尼亞克的《戲劇實(shí)踐》、圣埃夫雷蒙的《古代與現(xiàn)代悲劇》、坦普爾的《詩(shī)論》和《論古代與現(xiàn)代學(xué)問》、德萊頓的《諷刺詩(shī)的起源與發(fā)展》、蒲柏《批評(píng)論》中的部分詩(shī)節(jié),尤其是伏爾泰的《論史詩(shī)》、布萊克韋爾的《荷馬生平及其史詩(shī)述評(píng)》、約翰遜為《莎士比亞戲劇集》所作的序言和《詩(shī)人傳》中的部分章節(jié)、托馬斯·沃頓的《英國(guó)詩(shī)歌史》、赫爾德的《論莎士比亞》、維柯的《關(guān)于各民族的共同性新科學(xué)的一些原則》以及許多為“神秘的”“東方的”“原始的”和“哥特式的”詩(shī)人和詩(shī)作進(jìn)行辯護(hù)的論述。
另一種方法是哲學(xué)家和批評(píng)家開始探討各種藝術(shù)的基礎(chǔ),開始用“科學(xué)的”和“哲學(xué)的”方法分析人的本質(zhì)、思維活動(dòng)、藝術(shù)品、世界的性質(zhì)等。這類文論有德萊頓的《詩(shī)與繪畫之比較》、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家》、艾迪生在《旁觀者》雜志上發(fā)表的關(guān)于“想象的歡樂”的一些論文、布烏爾的《論作者的思維方式》、迪博的《關(guān)于詩(shī)與繪畫的思考》、萊辛的《拉奧孔》等,不一而足。
盡管他們采取的方法不一.討論的目的和內(nèi)容各不相同,但他們使用的一系列批評(píng)概念卻有相似之處。籠統(tǒng)地講,這些概念同屬于“新古典主義”的范疇。他們使用人們熟悉的分析與描述方法,試圖勾勒出不同詩(shī)體的規(guī)律、主題原則、結(jié)構(gòu)和風(fēng)格等。他們常用的術(shù)語有悲劇、喜劇、史詩(shī)、諷刺詩(shī)、頌詩(shī)、警句、牧歌、書信體詩(shī)、虛構(gòu)、寓言、風(fēng)俗、感傷、優(yōu)雅、平庸、粗俗、主題和方式、論點(diǎn)與布局、思維與表達(dá)、安排與表現(xiàn)、思想與情感等。其次,他們還使用更廣泛的術(shù)語討論文學(xué)的基礎(chǔ)、環(huán)境、起因、主題、目的、效果和特性。在這方面他們常用的術(shù)語有:自然、藝術(shù)、愉悅與說教、虛構(gòu)與判斷、想象與理性、獨(dú)創(chuàng)與模仿、模仿自然與奇異虛構(gòu)、一般性與特殊性、具有鑒賞力的人與普通讀者、樸素與雕琢、呆板與明快、真實(shí)與新奇、有規(guī)律與無規(guī)律、高尚與優(yōu)美、別致、荒誕等。毋庸置疑,僅憑這些術(shù)語當(dāng)然不能了解整個(gè)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的理論。我們也不能簡(jiǎn)單地認(rèn)為它們體現(xiàn)了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的“品味”。它們不過是一堆雜亂無章的術(shù)語而已。不過,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正是通過它們才得以描述其理論;或者說新古典主義的欣賞“品味”正是通過它們才得以確定。這些術(shù)語與早期的和后來的批評(píng)術(shù)語不同,它們是從古希臘批評(píng)家和古羅馬批評(píng)家賀拉斯、西塞羅和昆提利安的批評(píng)傳統(tǒng)中派生而來。正是這些術(shù)語所代表的概念體現(xiàn)了貫穿于整個(gè)新古典主義時(shí)期的詩(shī)歌理論和文學(xué)批評(píng)方式。
二、新古典主義的發(fā)展與演變
上文所謂貫穿于整個(gè)新古典主義時(shí)期的詩(shī)歌理論指的是這一時(shí)期在術(shù)語和概念的使用上始終如一,而不是指其恪守一套固定不變的原則或信條。新古典主義詩(shī)歌理論發(fā)展的成就之一是批評(píng)家觀念的轉(zhuǎn)變,即從注重“藝術(shù)”轉(zhuǎn)到了注重“自然”上。根據(jù)17世紀(jì)以及在此之前的批評(píng)家對(duì)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的一般理解,許多詩(shī)人和詩(shī)作并不符合古希臘和古羅馬批評(píng)家規(guī)定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當(dāng)時(shí)的新古典主義批評(píng)家由于受到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的激勵(lì)而為本國(guó)的這些詩(shī)人和詩(shī)作進(jìn)行辯護(hù)。在許多情況下,上述關(guān)于批評(píng)觀點(diǎn)從注重“藝術(shù)”朝著注重“自然”的轉(zhuǎn)變即始于新古典主義批評(píng)家進(jìn)行這種辯護(hù)的傾向。而正是這種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了批評(píng)界探討詩(shī)人環(huán)境背景的興趣,尤其是不同讀者的欣賞習(xí)慣、一般讀者的心理、詩(shī)的目的和表現(xiàn)方式等方面的興趣。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從探討“奇跡型”和“可信”的主題、“真正的”智慧和“虛假的”智慧、塑造圣徒的可能性與貼切性、悲劇中的愛情題材、三一律、悲劇和史詩(shī)中的韻律問題等,轉(zhuǎn)到了探論特定社會(huì)或者讀者群接受或不接受什么樣的詩(shī)作,不同體裁詩(shī)作模仿自然的結(jié)構(gòu)和本質(zhì)以及詩(shī)的真正作用是什么等問題。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重新評(píng)價(jià)詩(shī)作的風(fēng)氣日漸興起。批評(píng)界重新研究莎士比亞和荷馬的作品,因?yàn)檫@些作品富于想象力,而不是說理或?qū)W識(shí),也因?yàn)樗麄兊脑?shī)作活潑明快,而不是適度得體,富于創(chuàng)造性而不是一味模仿。通過重新考察原已確立的詩(shī)歌規(guī)則和標(biāo)準(zhǔn),批評(píng)家超越了詩(shī)人的“理性”“正確性”或者“判斷力”等問題,為實(shí)現(xiàn)詩(shī)作創(chuàng)作的目的而探討根據(jù)古代詩(shī)人創(chuàng)作實(shí)踐建立起來的詩(shī)歌規(guī)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問題。于是批評(píng)家們往往根據(jù)自然的法則和典型而不是根據(jù)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去尋找詩(shī)的真正的法則和典型。雖然從一開始就無人對(duì)“自然”的重要性提出異議,但拉潘、勒博敘、德萊頓、吉爾頓、丹尼斯、盧桑、戈特舍德、G·M·克雷欣伯尼、格拉維納等批評(píng)家關(guān)心的依然是藝術(shù)的法則和標(biāo)準(zhǔn),尤其是根據(jù)名詩(shī)和著名批評(píng)家從偉大的詩(shī)人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總結(jié)出的法則和標(biāo)準(zhǔn),而后來的批評(píng)家(如狄德羅、盧梭、約翰遜、楊、伯克、卡姆斯、雷諾爾茲、巴雷蒂、貝卡里亞、哈曼、赫爾德等)關(guān)心的是“理想”的自然。他們要么根據(jù)這種自然觀念總結(jié)出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法則”,要么根據(jù)這種自然觀念界定“藝術(shù)”。一般而言,充分體現(xiàn)這種自然觀念的古典名作一直受到批評(píng)界的重視。不過,到了18世紀(jì)初期,越來越多的批評(píng)家試圖通過揭示名作中的“自然”因素來解釋作品的“美”和效果。自18世紀(jì)中期以后,批評(píng)家對(duì)詩(shī)歌進(jìn)行評(píng)論時(shí)開始擯棄早已確立的“藝術(shù)”原則,并且開始擯棄根據(jù)經(jīng)典之作確立的原則。不論是“自然的”還是“藝術(shù)的”,文辭粗糙的還是精雕細(xì)琢的、古典的還是現(xiàn)代的,東方的還是古希臘的,“鄙俗的”還是“典雅的”,都在擯棄之列。批評(píng)家致力于考察作品的自然背景。到18世紀(jì)末期,根據(jù)新的“自然”觀念確立詩(shī)歌主題、結(jié)構(gòu)和風(fēng)格的真正原則,成了批評(píng)界的熱點(diǎn)。
這一時(shí)期批評(píng)界越來越關(guān)心詩(shī)人的個(gè)性力量和創(chuàng)作習(xí)慣,認(rèn)為這些與他所創(chuàng)作的詩(shī)歌有著因果關(guān)系。這種發(fā)展趨勢(shì)與把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從“藝術(shù)”轉(zhuǎn)到“自然”的發(fā)展趨勢(shì)并行不悖。從一開始,批評(píng)家就要求詩(shī)人既有天才(想象力)又有判斷力(學(xué)識(shí)),既是“自然的”,又是“藝術(shù)的”。古代的大批評(píng)家?guī)缀鯚o一不對(duì)詩(shī)人的神圣的靈感、天才的表現(xiàn)以及自然而單純的“創(chuàng)造性”極其重視。到17世紀(jì)末期,布烏爾、坦普爾等批評(píng)家已開始重視這些古代的藝術(shù)原則。他們?cè)噲D解釋不同時(shí)代、不同民族詩(shī)歌的差異性。他們研究氣候條件、地理狀況、政治體制、歷史事件、詩(shī)人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等對(duì)詩(shī)作的影響,也研究不同種族、不同民族和不同語言背景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心態(tài)和習(xí)慣,尤其是其各個(gè)發(fā)展階段上的固有區(qū)別。當(dāng)然也有一些批評(píng)家開始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時(shí)代和不同社會(huì)的詩(shī)作的共性。這些研究激發(fā)了人們探索詩(shī)人的思維活動(dòng)和行為的興趣,而在此之前,在詩(shī)歌“藝術(shù)”的研究中詩(shī)人總是處于次要位置上。到了18世紀(jì)末期,大多數(shù)詩(shī)歌理論家都將詩(shī)人置于研究的中心。當(dāng)然這種“中心位置”并不是絕對(duì)的。他們只有討論主題、體裁、風(fēng)格和作品的意義時(shí)才想起詩(shī)人。總的來說,大多數(shù)新古典主義批評(píng)家都認(rèn)為,詩(shī)的意義取決于詩(shī)在讀者心中產(chǎn)生的效果,而不取決于詩(shī)人自已。
讀者并不是千人一面的。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的第三個(gè)重要方面表現(xiàn)在它對(duì)讀者欣賞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改變了原來關(guān)于“讀者”的許多重要觀點(diǎn)。盡管在這個(gè)問題上,批評(píng)家并未試圖建立一套新的價(jià)值體系,但是到了18世紀(jì)中葉,他們不僅有意拋棄早已確立的、具體的詩(shī)歌法則,而且開始擯棄關(guān)于“讀者”的一般概念。在早些時(shí)候,批評(píng)界關(guān)心的要么是一個(gè)特定社會(huì)不同讀者的要求——這些要求也許是隨意的,但卻不是過分的(據(jù)高乃依和羅伯特·霍華德的論述),要么是具有一定文學(xué)素養(yǎng)和判斷力的讀者的要求(據(jù)沙普蘭、拉辛、伏爾泰、德萊頓、丹尼斯、艾迪生、穆拉托里、福爾內(nèi)等人的論述),要么研究一個(gè)“自然”人的自動(dòng)反應(yīng)(據(jù)伯克、賴德、D·斯圖爾特、貝卡里亞、盧梭等人的論述)。這一時(shí)期許多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有其共同之處,它們構(gòu)成了探討讀者欣賞問題的基礎(chǔ),同時(shí)也推動(dòng)了對(duì)這個(gè)問題的進(jìn)一步研究。為了合理地解釋不同社會(huì)和時(shí)代產(chǎn)生不同的題材和風(fēng)格的現(xiàn)象,有些批評(píng)家認(rèn)為,我們不僅需要承認(rèn)詩(shī)人的“修辭”背景(個(gè)人天賦、受教育程度、讀者的特殊要求等)的差異性,而且要承認(rèn)在一個(gè)詩(shī)人和他的讀者身上可能存在著一種基本的人性(不同的氣候條件、地理狀況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正是形成不同的詩(shī)人和不同的讀者的主要因素);有的批評(píng)家覺得可能還存在著一種理想的人性或社會(huì),不同的社會(huì)要么是從這種理想社會(huì)脫胎而出,要么正朝著這種理想社會(huì)發(fā)展;也有的批評(píng)家將上述觀點(diǎn)糅合在一起探討讀者的欣賞問題。無論如何,這些探討旨在通過對(duì)不同讀者或者“最明智的要求”的分析,為那些似乎違反了詩(shī)歌藝術(shù)的“原則”和“標(biāo)準(zhǔn)”的作品進(jìn)行辯護(hù)。布瓦洛1674年發(fā)表了他翻譯的朗吉努斯的《論崇高》,并于1693年發(fā)表了他的《關(guān)于〈論崇高〉的思考》。此后,批評(píng)界開始關(guān)注朗吉努斯的這部批評(píng)文獻(xiàn)。批評(píng)界當(dāng)時(shí)對(duì)《論崇高》的理解還很膚淺。批評(píng)家討論崇高之藝術(shù)時(shí)并未強(qiáng)調(diào)讀者的差異性。正是在布瓦洛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批評(píng)家撰文探討讀者美學(xué)反應(yīng)的普遍原則。到18世紀(jì)末期,這種探討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潮流。
隨著“朗吉努斯熱”的不斷升溫,整個(gè)歐洲的文學(xué)觀念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意義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對(duì)朗吉努斯詩(shī)論的探討本身。新古典主義批評(píng)家起初關(guān)心的是體裁和與體裁相關(guān)的技巧問題,這時(shí)已將興趣轉(zhuǎn)移到藝術(shù)和自然的“質(zhì)量”上面,即將興趣從“技巧詩(shī)學(xué)”轉(zhuǎn)到了“質(zhì)量詩(shī)學(xué)”。朗吉努斯分析崇高之藝術(shù)時(shí)并不認(rèn)為特殊的體裁與藝術(shù)質(zhì)量是有關(guān),崇高的特征存在于散文和詩(shī)歌等各種體裁的文學(xué)作品中。但由于布瓦洛、德萊頓、丹尼斯等早期新古典主義者試圖使朗吉努斯的觀點(diǎn)形成體系,因而區(qū)分體裁在那一時(shí)期是必要的。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的興起和發(fā)展既是眾多的批評(píng)家探討朗吉努斯詩(shī)論的結(jié)果,又是批評(píng)家對(duì)不同時(shí)代、不同民族的詩(shī)人和作品進(jìn)行比較研究的結(jié)果,同時(shí)也是批評(píng)家從“哲學(xué)”高度探討藝術(shù)的普遍基礎(chǔ)的結(jié)果。到了18世紀(jì)末期,除萊辛之外批評(píng)家探討詩(shī)歌體裁的興趣已基本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對(duì)詩(shī)作的“抑郁型”或“英雄式”等質(zhì)量因素的區(qū)分。無論是進(jìn)行比較研究還是針對(duì)個(gè)別的詩(shī)人和作品進(jìn)行研究,通過這種質(zhì)量上的區(qū)分,我們都能對(duì)詩(shī)人或詩(shī)歌作出恰當(dāng)?shù)脑u(píng)價(jià)。布瓦洛和丹尼斯等早期的新古典主義者關(guān)心的是詩(shī)人的天才和學(xué)識(shí)在不同詩(shī)作中的表現(xiàn),而揚(yáng)、博德默爾、布賴廷格、穆拉托里等后來的批評(píng)家關(guān)心的是主題、思維和風(fēng)格。同樣,拉潘和德萊頓等早期的批評(píng)家認(rèn)為,不同的讀者喜愛不同的體裁或風(fēng)格,而博馬舍、體姆、哥爾德斯密斯等后來來的批評(píng)家認(rèn)為不同的讀者對(duì)主題的質(zhì)量和表現(xiàn)手法的喜愛不盡相同。
最后,在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發(fā)展的初始階段,尤其是在布瓦洛、德萊頓和穆拉托里的文章中,批評(píng)家討論主題和風(fēng)格時(shí)已開始強(qiáng)調(diào)睿智和判斷力、規(guī)則和不規(guī)則等作品的質(zhì)量因素。這說明他們已初步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是藝術(shù)的產(chǎn)物。在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發(fā)展的后一階段,尤其是在約翰遜、赫爾德和帕加諾的文章中,批評(píng)家討論詩(shī)人的思維和一般讀者的美學(xué)反應(yīng)的普遍性時(shí),便有意識(shí)地直接分析作品的崇高、優(yōu)美、真實(shí)、新穎等質(zhì)量因素。由于“藝術(shù)”和“自然”等術(shù)語常常出現(xiàn)于賀拉斯和朗吉努斯的詩(shī)論等關(guān)于技巧詩(shī)學(xué)和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的討論中,由于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的術(shù)語在關(guān)于“自然的”和“藝術(shù)的”爭(zhēng)論中獲得了特別的意義,因此,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發(fā)展到這個(gè)階段已經(jīng)沒有必要采用與眾不同的新術(shù)語了。
同樣,新古典主義詩(shī)學(xué)也就沒有必要克服其在討論讀者的反應(yīng)和需求等方面的特有傾向而取得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了。隨著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的興起,批評(píng)家探討詩(shī)人思維活動(dòng)的興趣日益高漲,他們開始強(qiáng)調(diào)“一般”人對(duì)作品的自然反應(yīng),而不是特殊讀者的需求。這樣,批評(píng)家便可以根據(jù)讀者的自然反應(yīng)來評(píng)價(jià)詩(shī)人的成就。由于批評(píng)家根據(jù)質(zhì)量詩(shī)學(xué)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能更容易地探討詩(shī)人的思維活動(dòng),于是,從新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的過渡也就順理成章了。因?yàn)樵诶寺髁x詩(shī)學(xué)中,首先“詩(shī)”被認(rèn)為是思想和表達(dá)的最佳質(zhì)量,而與具體詩(shī)作有所區(qū)別;其次,浪漫主義詩(shī)學(xué)不再?gòu)?qiáng)調(diào)讀者的反應(yīng),而主要關(guān)心詩(shī)人的心理和道德本質(zh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