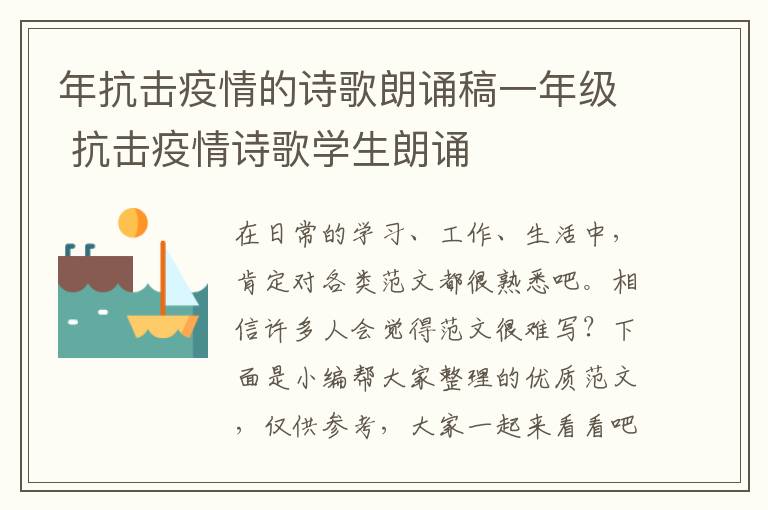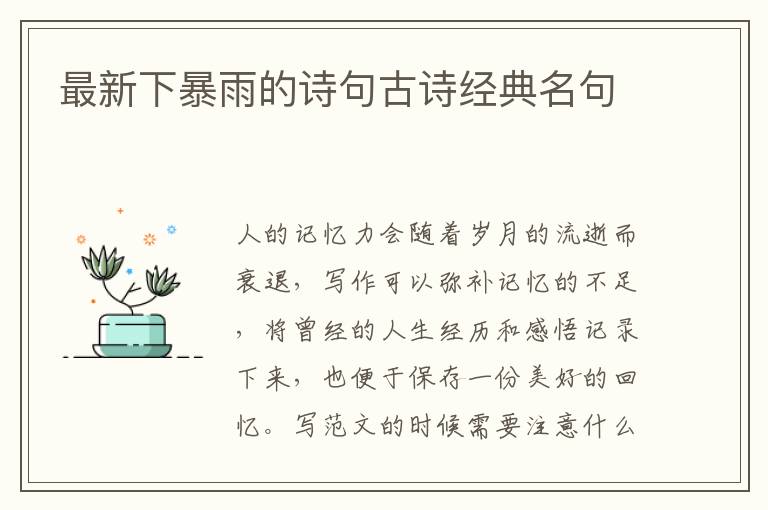人權(quán)與約法(節(ji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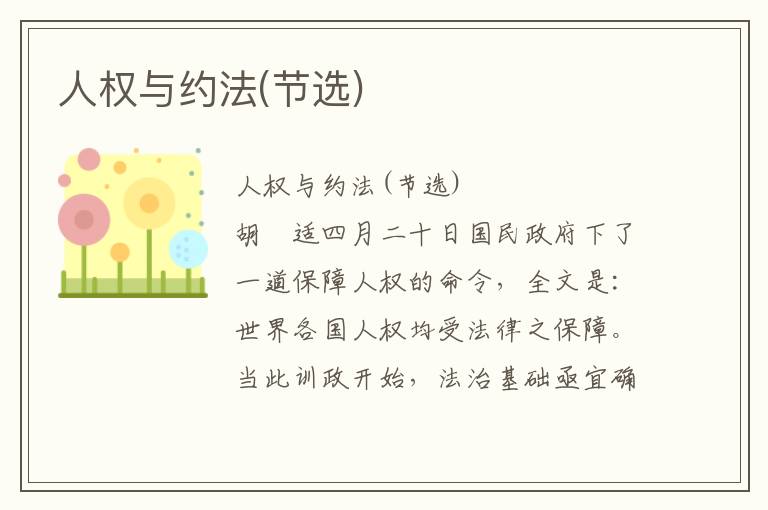
人權(quán)與約法(節(jié)選)
胡 適
四月二十日國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權(quán)的命令,全文是:世界各國人權(quán)均受法律之保障。當(dāng)此訓(xùn)政開始,法治基礎(chǔ)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quán)管轄之內(nèi),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違者即依法嚴(yán)行懲辦不貸。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體遵照。此令。在這個人人權(quán)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余剩的時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權(quán)的盛舉,我們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們歡喜一陣之后,揩揩眼鏡,仔細(xì)重讀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覺大失望。失望之點是:第一,這道命令認(rèn)“人權(quán)”為“身體,自由,財產(chǎn)”三項,但這三項都沒有明確規(guī)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幾種自由·又如“財產(chǎn)”究竟受怎樣的保障·這都是很重要的缺點。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個人或團體”,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機關(guān)。個人或團體固然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但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guān)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guān)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如今日言論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財產(chǎn)之被沒收,如近日各地電氣工業(yè)之被沒收,都是以政府機關(guān)的名義執(zhí)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對于這一方面完全沒有給人民什么保障。這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第三,命令中說,“違者即依法嚴(yán)行懲辦不貸”,所謂“依法”是依什么法·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權(quán)。中華民國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種種妨害若以政府或黨部名義行之,人民便完全沒有保障了。果然,這道命令頒布不久,上海各報上便發(fā)現(xiàn)“反日會的活動是否在此命令范圍之內(nèi)”的討論。日本文的報紙以為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會(改名救國會)的行動;而中文報紙如《時事新報》畏壘先生的社論則以為反日會的行動不受此命令的制裁。豈但反日會的問題嗎·無論什么人,只須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quán)的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剝奪,財產(chǎn)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為”了。無論什么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無論什么學(xué)校,外國人辦的只須貼上“文化侵略”字樣,中國人辦的只須貼上“學(xué)閥”“反動勢力”等等字樣,也就都可以封禁沒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我們在這種種方面,有什么保障呢·……我在上文隨便舉的幾件實事,都可以指出人權(quán)的保障和法治的確定決不是一紙模糊命令所能辦到的。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為都不得逾越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法治只認(rèn)得法律,不認(rèn)得人。在法治之下,國民政府的主席與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都同樣的不得逾越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國民政府主席可以隨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自然也可以隨意拘禁拷打商人了。但是現(xiàn)在中國的政治行為根本上從沒有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人民的權(quán)利自由也從沒有法律規(guī)定的保障。在這種狀態(tài)之下,說什么保障人權(quán)!說什么確立法治基礎(chǔ)!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權(quán),如果真要確立法治基礎(chǔ),第一件應(yīng)該制定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至少,至少,也應(yīng)該制定所謂訓(xùn)政府時期的約法。孫中山先生當(dāng)日制定《革命方略》時,他把革命建國事業(yè)的措施程序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三年)第二期為約法之治(六年)……“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quán)利義務(wù),及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quán)利義務(wù),悉規(guī)定于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司法者,負(fù)其責(zé)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革命方略》成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其后續(xù)有修訂。至民國八年中山先生作《孫文學(xué)說》時,他在第六章里再三申說“過渡時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說“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xùn)導(dǎo)民人,實行地方自治。”至民國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國革命史》時,第二時期仍名為“過渡時期”,他對于這個時期特別注意。他說:第二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nèi),施行約法(非現(xiàn)行者),建設(shè)地方自治,促進民權(quán)發(fā)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每縣于散兵驅(qū)除戰(zhàn)事停止之日,立頒約法,以規(guī)定人民之權(quán)利義務(wù),與革命政府之統(tǒng)治權(quán)。以三年為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革命政府之對于此自治團體只能照約法所規(guī)定而行其訓(xùn)政之權(quán)。又過了一年之后,當(dāng)民國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國大綱》時,建設(shè)的程序也分作三個時期,第二期為“訓(xùn)政時期”。但他在《建國大綱》里不曾提起訓(xùn)政時期的“約法”,又不曾提起訓(xùn)政府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后來的人只讀他的《建國大綱》,而不研究這“三期”說的歷史,遂以為訓(xùn)政時期可以無限地延長,又可以不用約法之治,這是大錯的。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雖沒有明說“約法”,但我們研究他民國十三年以前的言論,可以知道他決不會相信統(tǒng)治這樣一個大國可以不用一個根本大法的。況且《建國大綱》里遺漏的東西多著哩。如廿一條說“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tǒng)任免”,是訓(xùn)政時期有“總統(tǒng)”,而全篇中不說總統(tǒng)如何產(chǎn)生。又如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已有“以黨為掌握政權(quán)之中樞”的話,而是年四月十二中山先生草定《建國大綱》全文廿五條中沒有一句話提到一黨專政的。這都可見《建國大綱》不過是中山先生一時想到的一個方案,并不是應(yīng)有盡有的,也不是應(yīng)無盡無的。大綱所有,早已因時勢而改動了。(如十九條五院之設(shè)立在憲政開始時期,而去年已設(shè)立五院了。)大綱所無,又何妨因時勢的需要而設(shè)立呢·我們今日需要一個約法,需要中山先生說的“規(guī)定人民之權(quán)利義務(wù)與革命政府之統(tǒng)治權(quán)”的一個約法。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政府的權(quán)限:過此權(quán)限,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quán)的,無論是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我們的口號是: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chǔ)!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quán)!原載1929年4月10日《新月》第2卷第2期
〔鑒賞〕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原名嗣穈,學(xué)名洪骍,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現(xiàn)代著名學(xué)者、詩人、歷史家、文學(xué)家、哲學(xué)家。于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xué)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并開始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白話文章,后任該報編輯。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xué),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xué),于康乃爾大學(xué)先讀農(nóng)科,后改讀文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xué)研究院,師從哲學(xué)家杜威。1917年夏回國后任北京大學(xué)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xué),積極提倡“文學(xué)改良”和白話文學(xué),成為當(dāng)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時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并一度擔(dān)任上海中國公學(xué)校長。抗日戰(zhàn)爭初期,曾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1948年去美國。1958年后去臺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突發(fā)心臟病去世。此文寫在他擔(dān)任上海中國公學(xué)校長期間。1929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了一道人權(quán)保障的命令:“世界各國人權(quán)均受法律之保障。當(dāng)此訓(xùn)政開始,法治基礎(chǔ)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quán)管轄之內(nèi),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違者即依法嚴(yán)行懲辦不貸。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體遵照。此令。”政府下令保障人權(quán),而且似乎面面俱到,這當(dāng)然是好事。但胡適卻偏偏唱反調(diào),在此令頒布不久,寫下了《人權(quán)與約法》。文章講到的問題為:1.人治還是法治;2.在“訓(xùn)政”的招牌下胡作非為;3.維護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些言論揭示了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的本質(zhì)。批評最為切要之處是在第二點上,“命令所禁止的只是‘個人或團體’,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機關(guān)”,“但今日我們最感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guān)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guān)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點出了保障令所保障的人權(quán)主要不是個人或團體,而是頒布這個保障令的政府本身。所謂“訓(xùn)政”,是國民黨政府借用孫中山的思想行專制之實。孫中山認(rèn)為,由于民眾的覺悟不高,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經(jīng)過軍政、訓(xùn)政、憲政三個階段,即以軍事力量推倒專制、訓(xùn)練民眾的政治能力、達到民主憲政等三個時期。這樣的分期法雖有合理之處,但是漏洞頗大。專制者可以借口民眾無能而強調(diào)訓(xùn)政,實行專制獨裁。胡適以其犀利的眼光,一下子就看穿了國民黨政府的伎倆。胡適的文章發(fā)表在上海的《新月》雜志上,引發(fā)了一場轟動一時的“人權(quán)運動”。其友人羅隆基、梁實秋等人積極參與,先后發(fā)表文章于《新月》等雜志上,談到的內(nèi)容包括人權(quán)與憲法的關(guān)系、什么是人權(quán)、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等等。這些文章以后被結(jié)集收入胡適的《人權(quán)論集》中,于1930年1月由新月書店出版。著名學(xué)者蔡元培寫信給胡適,稱“大著《人權(quán)與約法》,振聵發(fā)聾,不勝佩服”(《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張謇之子張孝若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先生在《新月》所發(fā)表的那篇文字,說得義正詞嚴(yán),毫無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識見有膽量!這種浩然之氣,替老百姓喊幾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guān)系也極大。試問現(xiàn)在國中,還有幾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xùn)政府的話·”(同上)他還寫了一首詩贈予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感想與擔(dān)憂。以后胡適迫于國民黨的威脅,于次年辭去上海中國公學(xué)校長之職。可見其文章對當(dāng)時執(zhí)政者時弊的觸動。中國近代的人權(quán)思想,受西方“天賦人權(quán)”觀與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影響,在胡適之前又經(jīng)康有為、嚴(yán)復(fù)、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提倡,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的氣候。不過當(dāng)初人們關(guān)心最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而胡適講人權(quán)較多立足于自由主義基礎(chǔ)之上。他在美國留學(xué)期間所受教育,以及關(guān)于知識分子應(yīng)當(dāng)保持中立和獨立的一貫認(rèn)識,特別是他所接受的19世紀(jì)歐洲的個人主義思想,直接導(dǎo)致他走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他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就提倡自由獨立的人格和為我主義的個人主義,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使之得不到自由發(fā)展。他認(rèn)為,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和人格,應(yīng)當(dāng)成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張。斷言一個自治的社會,一個共和的國家,都應(yīng)當(dāng)使個人有自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若不允許個人有自由獨立的人格,“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個人在鑄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以后,就會產(chǎn)生同國家的惡勢力相抗?fàn)幍挠職狻KM吹降氖墙∪膫€人主義的真精神,即敢于同腐敗勢力抗?fàn)幍摹柏氋v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這基礎(chǔ)上胡適思考的人權(quán)與約法關(guān)系,主要針對人權(quán)如何在法律上獲得落實,以及如何得到政治體制層面上的保障等問題。他的揭示說明了一個道理,在民主、法治、不知人權(quán)為何物的國家里,非但不能對人權(quán)有所保障,還會在事實上成為人權(quán)實現(xiàn)的障礙。國民黨口頭上說要保障人權(quán),實質(zhì)上是在禁錮人們的思想,實行的只能是思想文化的專制。時至今日,中國已進入21世紀(jì),距胡適寫作此文已過去了八十余年。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的人權(quán)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中國有關(guān)人身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自由權(quán)等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許多內(nèi)容通過法律條文的方式被確定了下來。至于思想與言論自由方面,借助于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介入等多種方式、渠道得以很好的體現(xiàn)。若胡適在世,見到這樣的政通人和局面,一定會欣然命筆,重新寫出有關(guān)人權(quán)與約法方面的新篇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