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古蘭亭辨》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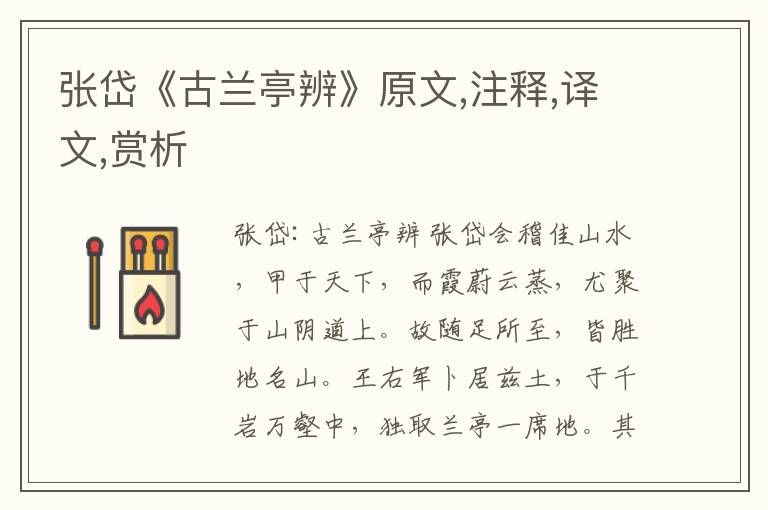
張岱:古蘭亭辨
張岱
會(huì)稽佳山水,甲于天下,而霞蔚云蒸,尤聚于山陰道上。故隨足所至,皆勝地名山。王右軍卜居茲土,于千巖萬(wàn)壑中,獨(dú)取蘭亭一席地。其景物風(fēng)華,定當(dāng)妙絕千古。且余少時(shí)見(jiàn)蘭亭墨刻,巖巒奇峭,亭榭巍峨,曲水流觴,浴鵝滌硯。開(kāi)卷視之,不禁神往。
萬(wàn)歷癸丑,余年十七,以是歲為右軍修禊之年,拉伴往游。及至天章寺左,頹基荒砌,云是蘭亭舊址,余佇立觀望,竹石溪山,毫無(wú)足取,與圖中景象,相去天淵。大失所望,哽咽久之。故凡方外游人,欲到蘭亭者,必多方阻之,以為蘭亭藏拙。因此裹足不到,又六十年所矣。
今年又值癸丑。 自永和至今,凡二十二癸丑。余兩際之,不勝欣幸。因檄同志,于三月上巳,會(huì)于蘭亭,仿古修禊。是日天氣晴和,偕吾弟登子,輕身濟(jì)勝,陟嶺登巖。坐天章方丈,尋覽古碑。始知舊日蘭亭與天章古寺,元末火焚,基址盡失。今之所謂蘭亭者,乃永樂(lè)二十七年郡伯沈公擇地建造,因其地有二池,乃構(gòu)亭其上,甃石為溝,引田水灌入,摹仿曲水流觴,尤為兒戲。蓋此地撇卻崇山,推開(kāi)修竹,制度椎樸,景色荒涼,不過(guò)田疇中一郵表畷耳!且地方湫隘,亭榭卑污,蘭亭圖上四十二人大會(huì)于此,輿馬冠蓋,騶從多人,黑子彈丸,于何駐足?其為影射,不問(wèn)可知。
寺僧言此原非故址,半里外尚有古蘭亭焉。余與登子亂踏荊棘,急往視之。及至其地,偏頗僻仄,愈不足觀。傍有石門(mén),勒“古蘭亭”三字。余細(xì)視之,乃是入蘭亭之古道,蓋路也,而非亭也。還至方丈,復(fù)撿啇吏部碑文。言萬(wàn)歷三年,西蜀劉見(jiàn)蒿、王松屏諸公得地于崇山之麓,溯流曲折,稍存永和之舊。捐金若干,委寺僧修葺。有亭翼然,匾曰“蘭亭遺跡”。后建廳事五間,以供宴會(huì)。曾不多時(shí),寺復(fù)摧殘,亭亦旋廢,其基址亦無(wú)所考矣。
余謂登子曰:“右軍,文人也,韻人也。其所定亭址,必有可觀。盍于荒草叢木中櫛比尋之?”乃于天章寺之前得一平壤,右軍所謂崇山峻嶺者有之,所謂清流激湍者有之,所謂茂林修竹者有之,山如屏環(huán),水皆曲抱。登之招手呼曰:“是矣!是矣!”乃席地鋪氈,解衣盤(pán)礴,幽賞許久,日晡方歸。
余謂蘭亭古跡,埋沒(méi)千年,一如蘭亭真本,辨才死守,什襲藏之,不許人見(jiàn)。后被蕭翼賺出,走至半途,袖中偷看,遍地花開(kāi)。此是寺中故典。余急欲于此地建一草亭,還其故址。一為蘭亭吐氣,一為右軍解嘲;亦猶梁上蘭亭,被余、登子等閑賺出之也。亭名墨花,竊附蕭翼。
本文選自張岱的《瑯?gòu)治募贰x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等大會(huì)于蘭亭,以事修禊,作《蘭亭集序》紀(jì)其盛,文章、書(shū)法,并稱(chēng)雙絕,蘭亭也從此著名。隨著時(shí)代遷延,到了明代,蘭亭故跡已經(jīng)迷失。張岱此文,就是為尋繹古蘭亭遣跡而作,雖題為“辨”,卻并不作枯燥的考證和說(shuō)理,而是描山摹水,情趣盎然,是一篇優(yōu)美的山水散文。全文可分三部分,分別寫(xiě)了作者一生中三個(gè)階段對(duì)蘭亭的理解和與蘭亭的因緣。
第一部分記“少時(shí)”的作者未見(jiàn)蘭亭故跡之前,蘭亭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張岱是紹興人,對(duì)家鄉(xiāng)的山水風(fēng)物情有獨(dú)鐘,故稱(chēng)“會(huì)稽佳山水,甲于天下”。“而霞蔚云蒸”幾句,使人想起王羲之之子王獻(xiàn)之對(duì)山陰道的贊美:“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fā),使人應(yīng)接不暇。”(《世說(shuō)新語(yǔ)·言語(yǔ)》)作者推想,在這樣的勝地名山之中,王羲之選中的蘭亭,定有“妙絕千古”之處。而且作者還見(jiàn)到過(guò)描繪蘭亭的墨刻圖,畫(huà)中景象,進(jìn)一步印證了他的推想,這使他心神向往。“不禁”二字,貼切地刻劃出少年人純真美好的憧憬和躍躍欲試的沖動(dòng)。
第二部分寫(xiě)作者十七歲初游蘭亭舊址。這一年論干支紀(jì)年,歲在癸丑,正是王羲之修禊之年,作者特地選擇這樣一個(gè)有紀(jì)念意義的時(shí)日游蘭亭,可見(jiàn)他對(duì)心目中的這塊“圣地”是多么珍惜,對(duì)初游蘭亭是多么重視,想著多年神往的蘭亭就要出現(xiàn)在自己眼前,他的心情又該是多么激動(dòng)!然而,他所見(jiàn)到的卻是一片“頹基荒砌”,“毫無(wú)足取”的“竹石溪山”,這與他少年時(shí)所看到的“圖中景象”,與他心目中的蘭亭,判若兩個(gè)世界,怎能不使作者“大失所望”!期待越是殷切,失望的打擊就越大。內(nèi)心珍藏多年的美好形象幻滅了,因而萬(wàn)分痛心,“哽咽久之”。對(duì)這次游歷所見(jiàn),他沒(méi)有多寫(xiě),也不愿多寫(xiě)。他阻止別人去游蘭亭,也是為了不讓別人體驗(yàn)自己的痛苦心情,保護(hù)蘭亭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印象。這舉動(dòng)也可看出張岱年青氣盛,任情率直的性格。
第三部分是年逾古稀的作者與蘭亭闊別六十載后,舊地重游。這次游蘭亭的契機(jī),還是癸丑年,但和初游蘭亭的情形有所不同。初游時(shí)不過(guò)“佇立觀望”,掉頭就走;這一次則謁碑訪僧,追流溯源,靜觀默察,游得很細(xì)心。此時(shí)作者的年齡、修養(yǎng)、心情都已進(jìn)入老境,而且有了足夠的心理準(zhǔn)備,因此不象第一次那樣倉(cāng)促和沮喪,但尋覓蘭亭古跡的愿望卻顯得更加迫切。他先是冷眼觀察所謂的蘭亭遺跡,探究它的由來(lái),一一考辨其環(huán)境、布局、構(gòu)造、氣度,斷定其為“影射”,認(rèn)為如此椎樸荒涼,“不過(guò)田疇中一郵表畷(管理農(nóng)田小官所住的野外小舍)耳”。當(dāng)寺僧告知“半里外尚有古蘭亭焉”,作者喜出望外,“亂踏荊棘,急往視之”二句,生動(dòng)形象地寫(xiě)出了他急切的心情。但此番所見(jiàn)到的“愈不足觀”迫尋古跡的線索也茫然無(wú)緒了。然而,經(jīng)過(guò)這兩次尋找,作者頓然有悟。他不象年青時(shí)那樣掃興而歸,而是決計(jì)拋卻前人,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積累和審美經(jīng)驗(yàn),依照自己對(duì)王羲之和蘭亭的理解,直接到大自然中去發(fā)現(xiàn),去挖掘。終于心與境遇,“得一平壤”,《蘭亭集序》中所描寫(xiě)的“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歷歷在目。作者為自己的發(fā)現(xiàn)而欣然歡呼,席地而坐,怡然幽賞,盤(pán)桓不去。作者并不刻意找什么殘?jiān)珨啾凇U池枯流來(lái)為自己的發(fā)現(xiàn)作佐證,在他看來(lái)這一切都無(wú)關(guān)緊要,重要的是這里的真山真水、精神氣脈是與心目中的蘭亭相通的,這里有蘭亭之美的真諦。
王國(guó)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有‘有我之境’,有‘無(wú)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wú)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這篇文章中的古蘭亭之于作者,就是一個(gè)“有我之境”。張岱尋覓蘭亭故跡的過(guò)程,正是追求物我合一,心境相融的完美境界的過(guò)程。他對(duì)那些所謂遺跡的考辨和唾棄,就是執(zhí)著于自己的審美理想;而一旦尋覓到了心中的蘭亭,一切論證就都是多余的了。也許本文算不上合格的考證文章,但它卻是篇不可多得的、充滿美的靈感的散文佳作。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用蕭翼從辨才和尚處賺取《蘭亭集序》真跡的故事,來(lái)比喻自己對(duì)蘭亭故跡的發(fā)現(xiàn),得意而不乏幽默。他那建亭命名的設(shè)想,也給讀者以遐想,情意濃厚,韻味深長(zhǎng)。








